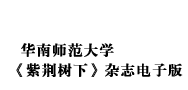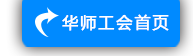汲汲生活的欢乐——评《冬牧场》之前的李娟 / 陈立群


读了《冬牧场》之后,我兴奋莫名,到处向人推荐李娟。澳门教师进修班的一位女同学附和了我,说:"我和我女儿都爱读她的书。我们觉得有趣极了。"我听得一脑门官司:《冬牧场》很有趣么?新疆籍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同学则说:“我更喜欢她之前的作品。《冬牧场》是为《人民文学》写的,有点用力过度。”
于是我又去读了《九篇雪》、《阿勒泰的角落》……我明白了。
这里的李娟不再忧国忧民。她只是一个快活的小丫头。疯丫头。没心没肺的傻丫头。
日子还是那么艰难。无论是对她们母女俩,来到新疆讨生活的两个没文凭没钱财的四川女人;还是对阿勒泰的土生土长的老乡,在森林与沙漠间辗转四季的牧民们。她俩做裁缝,当小贩,卖杂货……他们养羊、赶羊、接生羊羔、剥洗羊皮……大伙儿东奔西走,攘臂揎拳,全力以赴,但生活就像那条无比宽大却怎么也不合身的料子裤子,或者那顶塑料袋堵塞的四处漏风的帐篷,行动间,便破绽百出,处处都是致命伤。无可救药的蹇涩。
但她却那么地快活。她,和她的妈妈,和她们的阿勒泰邻居。她写她的妈妈,她外出游荡,发现了麻雀窝,回来向女儿炫耀:“你没看见真太可惜了,你不知道那多好玩!"女儿着急地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她老人家捂了脸,趴在床上一个劲儿地笑:'不告诉你,死也不告诉你,急死你!'”(《妈妈知道的麻雀窝》)她写她们住的塑料布帐篷:"屋顶上停满了鸟儿……我们在帐篷里愉快地生活,不时抬头看看透明帐篷上的那些调皮有趣的小脚印。……有时我妈妈会爬上柜台,站得高高的,用手隔着塑料纸的顶棚轻轻地戳着那些脚丫……我妈满脸的笑,但忍着不出声,鸟儿们跳到哪儿就戳到哪儿,想象鸟儿们纳闷奇怪的表情。"(《住在山野》)她写维汉两族的语言不通:“我外婆在炉边做早饭,大家一边烤火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恭维我外婆高寿、身体好,能干活……而我外婆一直到最后都以为他们在向自己讨米汤喝。更有意思的是,我外婆偶尔开口说一句话,所有人都立刻一致叫好,纷纷表示赞同,还鼓起掌来--哪怕她在说:'稀饭怎么还不开?'”(《交流》)她写山区道路的险峻:"到了下坡路,倘若此时那辆四面挡风玻璃全无的破车突然乱档,刹车失灵了,司机是断然不会告诉你的。他脸不变色心不跳,反而会更加高兴地大展歌喉,一边歌颂爱情一边飞快地转动方向盘从悬崖峭壁处险象环生地擦过,把汽车当飞机开。"(《行在山野》)--日子千疮百孔,她在这破裂处看到的却都是绽放的花朵。即使是遇上意图非礼的异族青年,那人那事也并不狰狞可怖,反而由她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各种讨伐,以及那心怀鬼胎的青年的尴尬、狡黠,凸出一幅可爱有趣的图画。这里,一切阴影退散,昏晦、黑暗只是万色万状的之一,不会吞噬什么,不会威慑什么。
因而在这样纯净的奔波生活里,她纤细灵敏的触角可以长长地探出去,猝然击中某些神秘的柔软的中心,让人冷不防地一颤。她写那极力挖洞逃走的兔子:“都说兔子是胆小的,可我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实是勇敢的,它的死亡里没有惊恐的内容。无论是沦陷,是被困,还是逃生,或者饥饿、绝境。直到弥留之际,它始终那么平静淡漠。面对生存命运的改变,它会发抖,会挣扎,但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兔子所知道的又是些什么呢?万物都在我们的想法之外存在着,沟通似乎绝无可能。”(《距离春天只有二十共分的雪兔》)她写那些手工织毯上的图案:“倘我能--倘我能用我的手,采集扎破我心的每一种尖锐明亮的颜色,拼出我在劳动中看过的,让我突然泪流不止的情景,再把它日日夜夜放在我生活的地方,让这道闪电,在我平庸的日子中逐渐简拙、钝化,终于有一天不再哽咯我的眼睛和心--那么,我便完成了表达。我便将我想说的一切都说出了,我便会甘心情愿于我这样的一生……可我不能!”(《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这种时候,她那缪斯祭司般的女诗人形象才偶尔一露峥嵘。
然而宇宙的奥义究竟是什么呢?也许还是那些世俗欢乐:闭塞操劳的转场生活中通宵达旦的托斯舞会,寂寥贫乏的姑娘们不停交互欣赏的新衣服,孩子们反复折叠又打开的破洞的白皮球……
向一位学长推荐李娟。学长略略一读,便向我说道,李娟太清浅,没经过磨砺,没法传达更深刻的内容。学长的意思,大概是嫌她对人生的沉重挖掘得不够深刻吧。但是,我总是想起那个著名的譬喻:后有狼逐,前有虎伏,悬于断崖上摇摇欲坠的枯枝,人贪婪地看着眼前鲜红欲滴的红果,伸出了舌尖……
那红果的滋味啊!那不正是我们贪恋的人生,一晌半晌的欢乐?
在我们的文学里--中国的,现代的文学,苦难遍地皆是:鲁迅、巴金、茅盾;余华,莫言,阿城……他们或揭发那已麻木的苦难,或控诉那压迫着的苦难。苦难是异己的存在,如癌细胞,吞噬、侵犯着人的正常生活。但在李娟笔下,苦难并不横亘在人的对面,表现自己为苦难。它只是广阔、奇妙的生活的一个无足为奇的构件。欢乐才是生活的主题。苦难与生活的其他诸多部分混杂一起,彼此撞击,迸出欢乐的火花。
饱尝艰辛,尽历苦难,贝多芬在《英雄》与《命运》之后,最终的天鹅绝唱却是《欢乐》。“在这美丽大地上,普世众生共欢乐;一切人们不论善恶,都蒙自然赐恩泽。”(席勒《欢乐颂》)
传达、传播欢乐,我相信,才是文学,艺术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