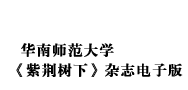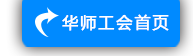现代女性的自我镜像——潘玉良自画像观后感 / 吴敏


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无论如何也绕不过性别文化的视角。当女性有机会走出深宅大院闺门绣房,接受新式教育,接触现实生活,用自己的眼睛观看世界,用自己的心胸体悟生命,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艺术才华得以显现,女性走出被书写、被描绘、被拍摄的"客体"位置,这时候,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就开始了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化就浮出了历史地表,人类文化也因此发生了质的变化。
鲜明而非隐晦的、丰富而非定型化的"艺术自我"是女性进入"现代"的特别突显的现象。文学领域里女作家大量的自叙传作品、美术界里女画家的自画像、电影领域里的女演员女导演和女性题材作品等,凭借艺术的镜像来观察、分析、表现自我,成为现代女性特别钟情的形式。这不仅仅是美学方式、艺术手段的探讨过程,也是思想、伦理、情感的寻觅过程,是女性自我认识和自我成长的过程。"自画像"是20世纪中国女性艺术图像衍变轨迹中的独特现象。
自画像在中国女性绘画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比例,统计可能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女画家在多大的程度上愿意在画布上展现自己和展现怎样的自己、愿意以怎样的公开方式显现自己,长久的自我凝视和自我成像过程对画家的自我认识意味着什么,女画家在追求"形似"的同时怎样变形勾勒自己的"神似"等,都是人们容易联想的相关问题。相对于五四以后为数不算多的女画家,潘玉良的自画像特别引人关注。这不仅因为她的自画像比较多,更由于其内潜的丰富涵义。
20世纪以前,中国女性如果有机会被显现于画轴书册,通常是圣母、圣女、女神、仕女的形象。清代画家余秋室描绘过柳如是的图像。柳如是,明末清初的歌妓才女,曾因诗画歌舞而名噪一时,性情刚烈,是清代诗人钱谦益的小妾。著名学者陈寅恪著有8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然而,这位现实生活中风采卓然的女性在男画家笔下端庄秀丽、神态温和,柳叶眉樱桃嘴,基本上是平民化的仕女图特征。
潘玉良的自画像,摆脱了女性被描绘时所通常带有的低眉顺目、庄重沉静、线条柔和的模式化图形。她的多幅自画像有着较为明显的写实风格。其构图有两种基本色调和情调,一种是阴暗的、沉郁的、幽怨的、哀伤的,另一种则是明艳的、绚丽的、有力的、高傲的,狭窄的空间和粗简的背景常常有怒放的红花和飘曳的繁花,人物脸上细长而黑亮的丹凤眼所投射出的忧郁、哀怨、凄清、凛然的眼神,让观众无法躲开、不能回避。墨黑、雪白、鲜红或绛红、明绿、靛蓝等颜色,是潘玉良许多自画像的主色调,呈现着冷与暖、明与暗、喜与忧的相互交织、对照、融汇的审美"复调"。
《自画像·醉》描绘的是女性独饮自斟的画面。"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把酒问青天"、"李白斗酒诗千行"似乎常常是男性的形象特征。潘玉良这幅自画像里的女子正在开怀畅饮,左手撑头似乎有些不胜酒力,右手抚着的右腿高高撑起,喝酒的场面却运用了匀称稳重的构图,红色的背景与微红的脸庞互相映衬,增添了欢畅的情绪。女子的笑脸微微低侧,仿佛在自喜自矜、品味陶醉。这个笑脸显然是对着自己的内心,而不与观众交流,似乎正是这样的自斟独饮,才带来了"开怀"的尽情放松的快乐。在这幅画里,孤独与奔放、寂寥与愉悦、敞开的胸膛与女性内心洋溢着的似乎只有自己才能明了的情热融为一体,这种"复调"在构图和道德上构成了对传统观念的挑战。
从1920年代开始,潘玉良不曾间断地为自己画像。潘玉良自画像最令人难忘的是女主人公的眼神。这些眼神多种多样,透露出现代女性丰富博广的情绪体验,可以用许多词汇来描述阅读观感,如幽怨、哀婉、凄凉、寂寥之类的,如愤怒、傲然、不屑之类的,也有平和、温柔、喜悦、欢快之类的。与自画像相联系,潘玉良还有大量的女性形象画作,女性相亲互恋的绘画,而且是大比例的裸女形象,另外还有多幅女性哺乳的母子图。这些图像中的女性大多有高挑的波浪形、显示着美丽又孤傲神情的眉毛和细长向上的眼睛,与潘玉良自画像中的女性很相似,不妨视为潘玉良的准自画像。《读书的女人》、《坐在椅子上的女人》、《披花头巾的女人》、《女人和猫》、《菊花和女人体》、《女人背影》、《姊妹相亲》等,背景较为粗糙含混,配色简单,不甚平滑的线条和不太"黄金比例"的体型,臀部宽硕,双腿粗壮,脚板脚趾厚大,显示着女性磅礴宽广的身体力量和情绪能量,有一种健康、阳光、与自然相仰合、不失柔情的阳刚之美。潘玉良显然赋予了她的女性形象以壮阔、雄强的身体力量,颂扬了原始的母性情感。正如《自画像·醉》一样,这些女性形象的头部大多低侧、仰侧、里侧或半掩着,眼神内倾,不与观众沟通。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可以把这些女性形象阐释为女性的身体欲望、自我欣赏、自我迷恋。她们不是欲望的对象,而是欲望的主体,她们为自己而存在,为自己的健康而自豪。没有挑逗、猥亵、羞涩,没有故作的妩媚、矫情、华丽。女性在潘玉良的视线和画布里,具有如此强壮、坦荡、雄浑而不失柔美、温情的自主力量,令人震惊。没有对女性诚挚的热爱、深切的同情,就很难有这样饱含热情赞颂的画像。即使用自恋、同性恋、甚至自我迷狂一类含有贬义的词汇来形容女画家的心理动机,也无损于潘玉良这些画作的艺术价值。尽管潘玉良的画风明显地受着西方现代油画尤其是巴黎画派和中国新白描体绘画技巧的影响,尽管潘玉良对于绘画人物的选择、在构图光线色泽的设计等诸多方面可以在中西比较文化的视野中去进行评价,尽管潘玉良把自己当作模特儿的绘画令人猜测她所可能存在的创作情境和窘境,然而,将这些画放在中国绘画历史、中国女性图像衍变的坐标里,不能不说,正是在潘玉良的笔下,女性真正成为了有自己绘画语言的主体,女性文化呈现出了"现代"的性质。
潘玉良的这些画与被"美化"的女性裸体画有很大的不同。英国的约翰·伯杰在《视觉艺术鉴赏》里分析了文艺复兴以来众多男性绘画和摄影杂志上的女性身体,如安格尔,其画面中的女性姿态、表情、服饰、场合等,常常故作妩媚、谄媚,作为被观察者,安格尔画中的女性总是温顺、华贵地面对观察她的男人作出反应,"在欧洲的裸像艺术中,画家观赏者--收藏者通常是男性,而画作的对象往往是女性。这不平等的关系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中。……女人的形象则是用来讨好男人的。"女性的真实身份被极度漠视,画面中的人体常常被美化,被当作情欲、诱惑、美色、自我满足的对象,男性画家从描绘女性的裸体中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却在道德上谴责她。
常言说,"颂其诗、读其书"应该"知其人、论其世",阅读理解绘画作品也应该纳入"知人论世"的思考维度。尽管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创作环境与艺术创作并不一定构成决定性的直线关系,尽管艺术作品有其独立的审美意义和多维的解析方式,但"知人论世"仍是解读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背景,尤其是潘玉良自画像这样的作品。潘玉良自画像所显示的"复调",不能不使观众更深地去体味这位女画家曲折抑郁而又渴望飞翔、渴望灿烂的生命。在潘玉良身上,存在着深刻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方面是无可躲避的时代、家庭、性别的创伤,另一方面却是源于自身的高超的心力、悟性、生命追求。在中国五四新文化环境中成长、在西方现代文明中熏染的潘玉良,无论如何也洗不尽旧时代给她的辱蔑,无论怎样也不能接受旧家庭给她的定位,为妓、为妾、流言蜚语、排斥挤压、穷困孤独与独立自主的生命姿态、高远的人生价值目标、聪慧的天分心性,交织在她的人生路途中;青春的热情与流逝、女性的梦想与无奈、诱惑与压力、开朗与抑郁,等等,融汇在她的生命印记里。潘玉良享寿83岁。她应该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自己度过那些与荣誉、光彩并存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清贫寂寞、孤苦潦倒的许多日子。高昂的理想追求与惨痛的现实折磨,不能不形成潘玉良作品里特有的审美"复调"。历史转折时期许多新女性的命运总是难于逃脱悲剧的色泽,正因为新女性有所守持、有所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才使她们的生命绽放异彩。潘玉良的自画像正是现代女性生命的镜像。
女画家以自我或女性为对象进行创作,将自我影像投射到自我以外的画面,把"我"客观化为"他者"来进行描绘,对自我予以变形、虚构、改造,这种创作过程能为画家建立新的视觉经验和心理感受,正如拉康所描述的情形:成长中的人(婴儿)由于注视镜子中的自我影像,将对主体自我、外在世界产生新的感知和认识,"镜子阶段的功能在于建立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多义关系",是同形确认、异形确认、自我卫护、自我迷恋、打破自我等关系。或许,对潘玉良而言,不断地选择自己作为凝视对象,经常将自我"他者化",这时候,创作自画像就不纯粹再是"美学"的意义。这些再现女性自我的的作品,使她能够转移、宣泄和升华生活中的情绪,创作的过程无异于疗伤、自我拯救、自我安慰的阶段,观看自画像的时刻也是沉思、反省、更新和自我确认的过程。这时候,艺术的镜像不仅映照、折射了女性的现实处境,同时也是女性自我成长、不断成熟的重要中介。对许多女性来说,艺术已不仅仅是美术本身,而且成为了自己的生命存在。在文学领域里,许多女作家也正是通过自叙传或准自叙传的写作,来解读、分析、疗救、宽慰自己和同伴,来宣泄苦闷,寻找理想,重组现实。
当然,对女性艺术的探讨研究,除了关注女性的自画像人物画,还应该关注女性其他题材、类型的画作,应该具体分析其"中性化"的艺术创作。绝端地从"性别"角度去肯定或否定"无性别"或"性别意识模糊"的作品,都不是对艺术的科学态度。对于中性化的艺术创作,历来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女性关注"小我"以外的世界才能获得大成就,有人则认为女性描绘社会题材就可能失去自我性别,难于体现女性主义的艺术风格。在文学领域里,曾经有过"我卖文字,不卖'女'字"(丁玲)、"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我写的是'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所共同面临的生存和精神危机"(张抗抗)的争议。性别意识突显的艺术创作或者着重以"大我"的视角来观察表现大千世界的作品,都各有价值,关键在于合乎情理的价值阐释。有人认为,潘玉良的作品还只能显示"女性意识的萌动",直到199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女艺术家而无女性艺术,更没有女性主义艺术,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出现是在1990年代以后,这大概也是可以商榷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英]约翰o伯杰《视觉艺术鉴赏》,戴行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法]拉康《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收入《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