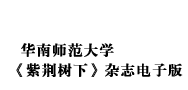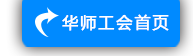灵魂的独舞——读《野草》


文/文学院 侯桂新
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孤独的,是鲁迅。
鲁迅写孤独最深刻的作品,是《野草》。
《野草》,多的是心底的独白,它是作者的喃喃自语,它原只属于鲁迅一个人。《野草》是散文诗,它的抒情主人公是这样一个形象:一个独坐于黄昏,手拈烟卷,精神疲倦,眼神朦胧,全身心沉入想象甚至梦幻的孤独的“瘦的诗人”。他沉酣于一个人的世界,这一世界对于他是自足的。他后来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孤独与沉默是一对好伴侣,在沉默中,人享有内心自我的完整世界;而一旦开口,他便于此远离,需要面对他人,投入到与此相异的外部世界。他又说:“我的心分外寂寞。”孤独与寂寞也是一对好伴侣,并常由寂寞所带来,虽然,寂寞的是心情,孤独的是灵魂。在寂寞中,在沉默中,人才更容易远离尘嚣,反躬自省,窥到自己心灵深处的潜隐。《野草》二十三篇(不计《题辞》),直接用第一人称“我”来写的共十六篇,但在整个全书中,始终找不到这样一个词:我们。“我”找不到同行者。即使在《死火》中,“我”与“死火”一并出到冰谷口外,鲁迅也没用“我们”,而是分为“我”和“他”。——《野草》写的,就是一个“我”的世界。

《野草》措辞隐晦,虚实相生,多用象征。但各篇当中,为作者首肯的,无论是“我”还是“他”,无论是人物还是物象,都常是孤零零的“一个”。在《求乞者》中,“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人与人之间互不相干。在《希望》中,“我”想去寻求“身外的青春”,“然而青年们很平安”,于是“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在将希望和绝望一一否定后,此文留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一个预备孤身奋战的警觉姿势或身影。更为典型的人物无疑是“过客”与“战士”,不论是寻求还是战斗,那脚步踉跄的和举起投枪的人都是单数的个人。再如物象,书中写到“寂寞的瓦片风筝”,写到“孤独的”“朔方的雪”,即便是《秋夜》,里面原有两株枣树,可写着写着只余下了一株,“他们”变成了“他”,倘非笔误,则可以说此处最明显地表现出了作者潜意识中的孤单心理。只有孤独的人,才爱写孤独的景,鲁迅对上述景物的敏感显然不是没有缘由的。
有人说,《野草》表现出作者对个性主义的否定和摆脱,并联系作者此前此后的思想与活动变化来加以说明。这种看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它至少包含了两点疑问:其一,什么是个性主义?其二,对个性主义该怎样评价?如果说个性主义的对立面是民族主义或集体主义之类,则二者并不构成绝对冲突,因为并不在同一层面上:集体主义更多指的是社会政治层面,与利益相关,个性主义则多指精神心理层面,侧重主体自我的张扬。如果是这样,个性主义似乎并不就是什么不好的东西,而集体主义倒是值得剖析一番。想依附一个集体而获得自我价值,结果却在集体当中泯灭了个人价值,这是中国历史上直到今天仍在一遍遍上演的戏剧。要行集体主义,先得有一个好的集体,这一点鲁迅看得很清楚。他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也就是在一个混沌阴暗的社会里对个人独立性与自我生命价值的珍惜。在《野草》中,鲁迅并没有“走出”个性主义。鲁迅之为鲁迅,就在于他始终独立不阿,从不会完全认同任何人任何集体。“过客”说:“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虽然,一个人“走路”太孤独。鲁迅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是否坚持个性主义,而在于他在保持个人独立性的同时,时刻不忘别的和自己一样的“个人”,也就是大众,并由此而产生出强烈的思想启蒙意识。在《狗的驳诘》中,“我”之所以会觉出“极端的侮辱”,并“一径逃走”,就是因为狗的驳诘虽然说的不只是“我”而是“人”,但“我”也是“人”中的一个,“我”这一个体承担了“人”这一集体或“类”的侮辱。倘不是这样,“我”的受辱感就无由产生。这一感觉的背后隐藏着的正是启蒙的意识。
鲁迅对自身孤独感所作的最深刻的书写,在《野草》中主要体现为那些写“梦”的篇章,尤其是那七篇以“我梦见”开头的作品。梦是人生最纯粹的独语,对梦的书写是个人灵魂最彻底的暴露。梦虽有时离奇怪诞,其中却往往包含了最深刻的真实,展示了人心日常难以窥视和把握的一面。因此,没有梦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没有梦的写作,是尚欠深入的写作。然而,写梦除了技巧,更需要的是解剖自我的勇气。没有材料能够证明《野草》中的“梦”哪些是“写实”,哪些是“象征”,但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除了《狗的驳诘》不太“真实”外,其余六篇仿佛都有“写实”的影子,尤其是《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等更是如此。这些梦表达的是社会批判与自我反省的内容,不必讳言,其中含有某些自我“阴暗心理”的揭示——从科学上说,这也是梦中人的潜意识作用的结果。即如《墓碣文》就反映了作者思想中一些虚无灰暗的成分。一般论者都以该篇最后一句话作为作者对这些思想情绪进行“否定”的证据,我倒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作者的一次“逃离”,因为,很明显,原文最后用的是“不敢反顾”几个字,“不敢”的情形下产生的愿望自然是“逃离”。何况,“虚无”岂是人可以轻易“否定”得了的,它往往与人生相始终,在不同的阶段,或浓厚或淡薄而已。更令人吃惊的是,“我”在梦中直到“死后”也还希望独处,不愿让人看见,“我十分高兴,因为始终没有听到一个熟识的声音。”
这样看来,鲁迅的孤独感不仅惊心动魄,深入骨髓,他自己并且有些喜爱上它了。
要探讨鲁迅孤独感的来源,自可涉及许多不同方面。从个人经历而言,少小时家庭的变故、横遭的冷眼、世态的炎凉使他过早地“少年老成”了;从社会环境看,黑暗统治下众多麻木的灵魂激发起他强烈的启蒙意识,然而在思想上他难以找到自己的“战友”,尤其是目睹了青年们的消沉之后;从个性气质上看,鲁迅“多疑”、“气大”,总之是一个相当内倾的人,这种人对孤独总是有着最敏感最切身的体验。或许,这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原因。而且,也许,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孤独的动物。在人心最深处,那块最隐秘的所在,总是留给自己一个人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更多的情形是:表面相知,背地分离;思想相通,灵魂分立。面对孤独,即使最负重望的“爱情”也无能为力,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在两颗心即将靠近相接的一刹那,人却突然借此反观到自己的灵魂,原来一直在寂寞独舞。两颗灵魂至多只能相互靠近,然而无法相融;即使合舞,分开来看也还是在独舞,还是存在无法消逝的距离。灵魂,原是谁的还是谁的。而真正的的诗人,其孤独较常人远甚——鲁迅即身列其中。
人注定孤独,但人又常常无法忍受孤独,尤其是长时期的。于是,人们便常将它隐藏起来,借助“自欺”。这自然是“怯弱者”。鲁迅的气质使他更易感觉孤独,而孤独(也包括寂寞和沉默)的积累也使他较常人更难以忍受。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有勇气直面这些,并与之进行碰撞相击,竭力要将它们驱逐,尽管这一过程饱含痛楚。“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自剖”之所以艰难,就因为它总是让人清晰地体验到一种耻辱和罪恶的痛感。然而,“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为免于悄无声息地灭亡,当然要选择激烈沉着的爆发。鲁迅很多时候都是在和寂寞、沉默与孤独作“绝望的战斗”。他自剖,或是解剖他人与社会,或是投入社会中作韧性的战斗,这些都同时也是借以摆脱孤独的方式——虽然,这些行动本身也都是在孤独地进行。后两者会带来危险,前者又会造成痛苦,然而他都顾不得了。他通过写梦严格地解剖自我,他要像枣树一样“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他要像战士一样举起投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哪怕与无物之阵同归于尽。“我一开口,便觉得空虚”,但他终于不能不开口,因为不能再沉默了。
这是勇者的品格。给鲁迅增添了一份勇气的是一个女性,她叫许广平。和许广平的相爱使鲁迅增长了勇气和力量,以至他明确表示《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自然,此处的“爱我者”可看作泛指)。如果为《野草》作一编年,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作品,许广平的爱情对鲁迅的鼓舞作用就更清楚了。可以发现,《两地书》的第一集写于1925年3月11日至7月底,而《野草》中的七篇“我梦见”作于1925年4月23日至7月12日,恰好在上述时间区间之内,这应当不是巧合。此前所作的十一篇,前六篇作于1924年秋、冬,其中《影的告别》、《求乞者》等篇重在反思自我;后五篇作于1925年初,单从《希望》(写于元旦)、《雪》、《好的故事》等标题和取材看,就已经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新的一年开始后,作者力争有所振奋,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更为强烈。但在此后一段时间,鲁迅并没有顺着这一思路往下写,而是中途插入了七篇“我梦见”,也许其间的原因正在于:与许广平的相识相爱,给了他足够的勇气和信心,使他能够写出这一在全书中需要用心最深用力最勤的部分,借此对过往的自己作一次彻底清理。写完这七篇“梦”后,一直隔了五个月,鲁迅才又重新开始写作《野草》,但风格渐变,有些篇章已经与杂文、政论接近了。从这一写作的“流程图”可看出鲁迅创作心理的几番变化,这自然与外界一些社会事件如女师大风潮、三·一八事变等不无关系,但与许广平的相爱无疑对他影响更大,这帮助鲁迅完成了一次阶段性的自剖,暂时减轻了孤独感这一心灵重负,并进而将笔墨更多地投向外部社会现实。想到这一点,我禁不住要替鲁迅感到庆幸和欣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鲁迅从此就永远告别了孤独,正如前文所说,没有什么可以消除孤独,事实上孤独是贯串了鲁迅一生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孤独成就了当时的鲁迅。幸耶?抑或不幸?
不管怎样,如果要从《野草》去接近鲁迅的身影和灵魂,凝视他处在那样的时代与社会中保持的是怎样一种“经典姿态”,我自认可以引用这样一段对“颓败线的颤动”的描写来加以说明:“……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不过,更为准确的应当是如这“朔方的雪”:
……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这是生命的独舞,灵魂的独舞,这也是鲁迅之舞。它灿灿地生光,并且,这光芒永存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