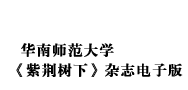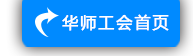此去经年,你一直在(生命科学学院 官党娟)



“人对往事的记忆就像锁在不同的抽屉里、舍不得丢弃的杂物,有些经过归档,有些无法分类,就那么一起掺杂地搁着,随着岁月的堆垒而尘封。某日不经意地打开一个抽屉,那被忘了、如同隔世般的旧事物便猛然回魂,又有了温度、呼吸和生命,过去与现在又接续上了。”(摘自阮义忠《抽屉里的浪花》)
“回忆这东西,它一直藏在你记忆里的某个角落,在你听一首歌、看一部电影、走过一个拐角的时候,它就会悄悄冒出来,在你以为自己已经忘记的时候,提醒那些你经历过的时光。”(摘自卢思浩《谁不曾浑身是伤谁不曾彷徨迷惘》)
从1993到2018,从求学到工作到今天,随着岁月流逝,一度以为已经遗忘,一度以为已经了无牵挂,一度以为已经激情不再,然而,就真的是哪怕一首歌,一个场景,一棵树,一朵花,一条路,一个拐角,都能让你觉得已经依稀的记忆,像电脑里加粗的初号字体一般清晰地展现在你脑海。于是,才发觉:此去经年,你一直在我深深的脑海里,华师。
每年9月,只要听到随处传来的“立正,向前看,正步走”,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带着一丝忧伤,一丝留恋,一丝迷离,脑海里浮现的是我的连长排长班长和我的排。骄阳,军姿,豆腐块,突然间,变得那么清晰。为了第二天能最快速地叠出最完美的豆腐块,我们曾一整晚和衣而睡,并且离那标准的豆腐块一定距离,生怕玷污了它似的。依稀仿佛中,耳朵里又清晰地听到了我的排长在问我:“你是哪里的?”“我是广东的。”“你是广东个屁!”至今,我还不曾弄明白:为什么在我的排长眼里,我就成了广东个屁?难道广东的屁比别地的屁开朗活泼上蹿下跳引人注目?
每逢五月附小门口的凤凰花开时,只需一眼,飘入脑海的,是那首“蝉声中那南风吹来,校园里凤凰花又开”毕业歌。皆因我们的1997年,毕业季,我,一个“广东的屁”,自撰自编自导了诗朗诵,把大学四年的点滴,全写在那我自认为是诗的诗里。而声情并茂的朗诵过程,是回忆,是不舍,是留恋,以至于把自己弄哭后,也成功地弄哭了我的同学们。毕竟,四年同窗,不说缘分,但有情谊。流溪河的山,大亚湾的海,鼎湖山的穿梭,白云山的蝴蝶,有人被一声“毛毛虫”吓得滚地兼且全身疙瘩,有人把海星做成项链,脖子一挂招摇过市,有人因为“无知”被槭树科的花叶扫出一身的疹子,更有人因为眼神不好,而让过敏的同学吃了6粒“息斯敏”,后来发现是吃6毫克(1粒),还好,被吃六粒的同学有惊无险,或许那“息斯敏”已离保质期甚远,又或者,那“息斯敏”就完全是假的。而那把6毫克看成6粒的同学,是我们红十字会的会员。
此去经年,你,一直在。一首歌,一部电影,一个场景,一个拐角,一条路,一棵树,一朵话,甚至一句话,记忆深处就像隐藏的宝藏,源源不断地能挖出宝来。
你,越来越美,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从1993到2018,我人生的黄金时代,都与你同在。关于你的记忆,于我,最深刻的印象,依然是1993-1997的那四年。对于一个人来说,青春是最容易被记住,无论精彩或是颓废,因为满腔热情,也因为满腹困惑。每每忆起,或欣慰,或遗憾,或懊悔。但是,青春,就像纹身,总是被紧紧烙在脑海,虽然很多时候都觉得已经遗忘,但只要有契机,记忆的闸门就会被打开。
那些年,我的华师,我的大学,我的青春。快乐,有趣,新颖是主角。风雨操场,水上餐厅,教工俱乐部,电教厅,生物园,生物系楼(现美术学院画室),东四宿舍(现心理学院),东九宿舍,一个又一个的建筑,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情怀。
因为有趣,所以记取,因为青春,所以铭记。站在当年的“今天”,我无法想象自己现在的“未来”,然而,站在现在,回想当年,却能让我不自觉地嘴角上扬。青春四年,你给了我太多好的记忆。生物系楼,承载了我们获取知识的种种姿态,种种啼笑皆非。生化实验课,唾液淀粉酶活力测试,所有同学都来问我要口水,现在脑补当年的那个场面,都觉得很壮观。原来,我的口水里唾液淀粉酶活力强大。要想得到好的实验结果,要想试剂颜色完美,要想实验报告能拿优+,必须得有好的唾液。动物生理学实验课,我摇身一变“刽子手”,蚯蚓,鸽子,鲫鱼,青蛙,兔子,无论是开膛剖肚,还是静脉注射,操刀的那一个,都是我。其实,在家,我是个连鸡都杀不死的人。人体解剖课,黄康华老师会带着我们去观摩尸体,一具被福尔马林浸泡着的男尸,已经是开膛剖肚的,时间太久,都不记得那尸体是不是各种器官都还齐全,只知道是一具身高1米8的男尸。当有同学每次都请假,当有同学从观摩室出来就狂吐,当有同学上完这个课一周甚至一个月不敢吃肉,我,每次课都是离那具男尸最近的,上完课依然大吃大喝的人。 儿童性心理选修课堂上,我们1米8几的张祥镛老师,用抑扬顿挫的声调,以及出神入化的,跟他个头压根不搭的肢体动作,给我们讲述“生男生女”的秘密时,满堂哗然。
我的大学,我的青春,我的华师,除了学习,就是娱乐。那时的我酷爱看电影,也有跟我一样酷爱的电影的同学。而承载我和我的同学们电影情怀的地方,就是电教厅。那时的电教厅,每到周末(周五周六),就是放映电影,两块钱一张票,但票上没有座位号,完全靠占位。为此,我经常不吃晚饭,老早就去排队,不是排第一也是排第二,怀抱着一堆书,不是为了学习,而是当我冲进电教厅时,经验老到地直奔最佳位置,然后随手一甩,怀里的书本一字散开,去到了各自的位置上——我这是帮我的同学们占位。因为占位,还跟男生吵过架,但最后吵赢的是我,还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东四,是我们大学前两年的宿舍。那是一栋两层的苏联式建筑,门对门,二楼楼道两端,都有个大门,门外是个阳台。阳台的存在不是重点,重点是阳台的两扇木门,总是关不紧,或关不上,每逢有风吹过,都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真是有点阴森得可怕。就因为这,我们宿舍七个女生,在我的“以身示范”下,都多准备了一个塑料盆,碰到实在要起夜的情况,都不出宿舍门,直接就在宿舍解决了。尴尬?比起只身一人大半夜去上公厕的境况,何来尴尬?
厕所是公共的,是没有门的半开放式的。而冲凉房就完全是敞开式的,就是水泥和砖砌出来的一个个隔间。开放点的,脱光了直接洗,羞涩的,会在冲凉间门墙上挂个帘子,我,属于前者,哈哈!这开放式的冲凉房,经常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并不是因为那一具具充满活力的青春胴体,而是因为那些声高八度的 “求救”话语:“张蕾,帮我拿一下我的毛巾。”“你不会自己来拿啊?”“我已经湿身了。”一听这普通话的表达语序,就知道这湿身者绝对来自广东。
那时,东四宿舍的唯一入口处有个传达室,每到周五周六晚上,传达室最热闹,而传达室的广播更是。因为不能随便进入,尤其是男生,所以这属于恋人相会,朋友相聚的周五周六夜晚,传达室挤满了人,有来寄放东西的,有来找人的。每当这时,我们这些没有人可会可聚的,就在宿舍里心不在焉地看着各种言情小说,亦舒,岑凯伦,琼瑶,都是那时我们的最爱。但是,那此起彼伏的找人广播,真是有点让我们烦躁,于是,每当听到某个有趣点的名字,我们就会在宿舍里鹦鹉学舌地也叫喊起来。以至于,某一天才发现,有一个叫“刘裘里”(音译)的,在广播里出现的频率最高,或许,仅仅只是因为每次广播响起这个名字,我们就会在宿舍高声地喊:“求求你,求求你,快下来!”然后,笑得毫无姿态地仰倒在床上。很无聊,是吧?可,这就是青春啊。
东九,我们大三大四时宿舍。那时住一楼(实际2楼),宿舍阳台正对陶园东门,因此经常被陶园飘来的饭菜香“毒害”。那时,作为师范生,国家每月补助我们每个学生150元。对于我们女生来讲,150元一个月一般是吃不完的,但我是三班的,所以我的全光,甚至每到月底,几乎每顿午晚餐靠5毛钱的炒粉撑过去,因为我们班某个男体特生养不活自己,我的150元,几乎一半养了他。并且,都是公开的秘密,因为那男生每到饭点,就会在东九我宿舍阳台下面,狠狠地喊上一句:“官党,饭卡。”(其实我已经不记得大三大四时是用饭卡还是饭票,大一大二时是用饭票的。)用自己半个月伙食费养着的男生,他却不是我的恋人,就只是我的哥们,哈哈哈哈!这让人遐想连篇的情景,恐怕只会发生在我身上。
无放肆,不青春。我的大学,我的青春,我的华师。在你的怀抱里,我们除了学习,偶尔,也犯点小错。周末的夜晚,一堆同学外出压马路,晚归,然后只能爬宿舍大门。东九的大门,废了我一身衣服。某一晚爬门,是很顺利的,但是,那天,那可爱的大门,刚被刷了新漆,还是红色的,而我,穿一身白。所以爬完大门,就报废了一套衣服。犯错,果然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东十九,我的男同学们的故事更精彩。他们晚归,没门可爬,他们爬水管,据说之前是屡屡得手的,直到某个晚上,无论谁,爬到一半,就滑溜溜地往下掉,不管怎么折腾,都爬不上去。就在他们纳闷之际,看门口的宿管大叔出来了,很是得意地,却也幽幽地来了一句:“爬不上去了吧?我还能抓不住你们?我可是在那水管上倒了一桶花生油咧!”为了抓住夜归的我的男同学们,大叔可真是破费了呀,但他高兴,因为被他抓住的我的男同学们,全被通报批评。犯错,果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岁月就像沙漏,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一天一天变老,将至生命的尽头。而你,一天一天变美变好变强大,迎来送往,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人才。“立正,向前看,正步走”的口号声依然在每个九月响彻校园,灿烂的凤凰花依然在每个五月绽放。
从1993到2018,我的大学,我的青春,我的工作,我的中年,我人生的黄金时代,都跟你同在。任由岁月变更,此去经年,你,一直在,在我那颗平静跳动着的心里,在我深深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