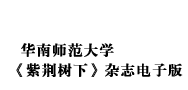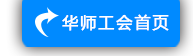逝去的“屋里的安琪儿”与另一种女人故事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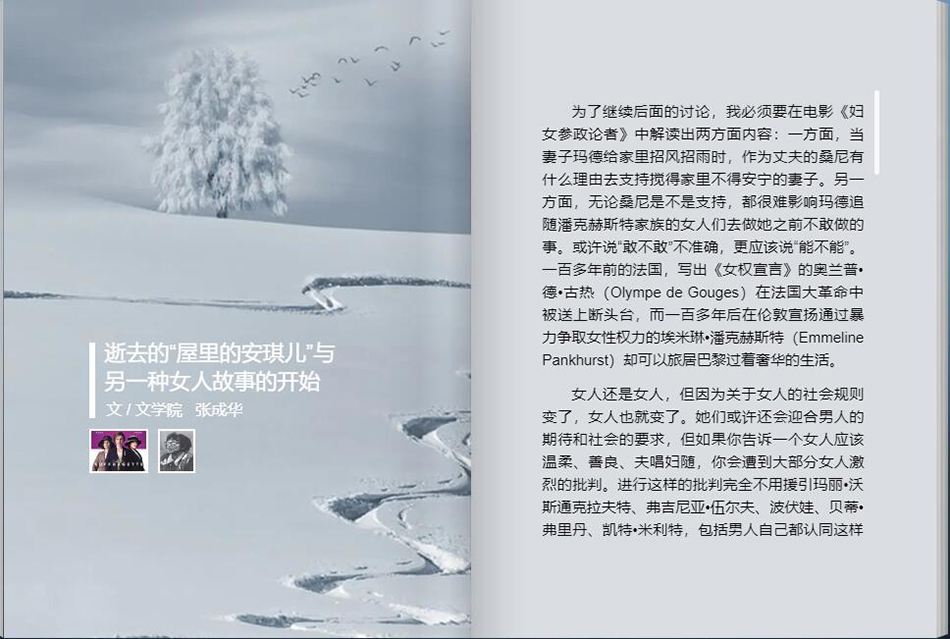
为了继续后面的讨论,我必须要在电影《妇女参政论者》中解读出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当妻子玛德给家里招风招雨时,作为丈夫的桑尼有什么理由去支持搅得家里不得安宁的妻子。另一方面,无论桑尼是不是支持,都很难影响玛德追随潘克赫斯特家族的女人们去做她之前不敢做的事。或许说“敢不敢”不准确,更应该说“能不能”。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写出《女权宣言》的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而一百多年后在伦敦宣扬通过暴力争取女性权力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却可以旅居巴黎过着奢华的生活。
女人还是女人,但因为关于女人的社会规则变了,女人也就变了。她们或许还会迎合男人的期待和社会的要求,但如果你告诉一个女人应该温柔、善良、夫唱妇随,你会遭到大部分女人激烈的批判。进行这样的批判完全不用援引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弗吉尼亚·伍尔夫、波伏娃、贝蒂·弗里丹、凯特·米利特,包括男人自己都认同这样的要求是在对女人进行规训和束缚。尽管大多数女人都没读过伍尔夫,但这不影响她们要杀死“屋里的安琪儿”,做真正的自己。
如果前现代的女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还只能是依附男人(丈夫、儿子)或者像花木兰一样以男性的面貌出现,现代女性则像阿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所说的被抛掷在双重的偶然性中:成为女人是偶然的,成为什么样的女人也是偶然的。换句话说,在前现代社会,一个女人应该温柔、善良、妩媚、善解人意,成为合格的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那么,在现代社会,女人自己既可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可以选择从事什么职业。如同开始解释《妇女参政论者》时所说的,无论男人/丈夫是不是支持,都无法改变这一总体的状况。
在现代,女人可以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并且,女人必须要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去成为真正的而不是别人要求的女人;或者说,因为成为了自己,她就必须要讲一个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可以是宏大的,也可以是卑微的;可以独属于自己,也可以与别人的故事纠缠在一起。
当然,上面说的只是总体上,具体到每个人或许是另一种情况。

事实上,女人们更关心的不是能不能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尽管我认为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都重要,而是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女人讲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要比男人遇到更多的困难;第二,女人的故事要受到更多的挑剔。正如我所说的,我认为女人能不能讲一个故事更重要,但却没法讨论太多,否则很难逃脱各种刁难。就个人来说,我也不想对第一个问题讨论太多。不过,如果不讨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恐怕没法讨论。尽管我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
事实上,对女人来说,故事展开的阻碍不在于男人的阻止或者粗暴的打断,也不在于伍尔夫所说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和每年500英磅的收入,而在于个人故事与其他人/其他故事的关系。女人更多的被看作也更习惯于成为故事的背景或完全依附于另一个故事。这里的其他人/其他故事包括家庭、丈夫、兄弟、孩子乃至经济、政治、历史等更宏大的层面。或许,让女性故事从属于其他故事的核心法则或者不二法门是奉献。这种奉献原则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故事是沉默的,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显现出来:一种情况是故事结束,我们去反思这个故事;另一种情况是这个沉默的故事在另一个故事中获得升华。奉献当然可以产生强烈的意义感。但问题是,第一,奉献成为唯一的法则;第二,奉献本身是沉默的,只能从另一个故事获得反向解释。
当然,任何一个故事都需要被解释: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相对于男人,女人的故事往往会获得更多的挑剔。一方面,人们除了对故事感兴趣,也对这个故事如何发生感兴趣。与之相关的另一方面是人们总是从性别的角度解读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我跟徐珊老师讨论过的例子是为了爱情嫁给远方的女性。这个故事总是会被从后果解释当然也是批判最初的选择。但是,这个故事跟一个男人选择了一个理想的女人,但这个女人最终将他的理想击的粉碎有什么区别?或者,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女人独有的故事?
对于文学专业的人来说,我们至少认同这样一个观点:解释既是故事意义生发的途径,也是歪曲故事意义的方式。当女人的故事获得更多解释时,也就需要经得起更多的挑剔和歪曲。正是因为这些挑剔和歪曲在淹没这个故事之于其本人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对任何一个故事来说,解释都会将其剥离原初的语境以及让其成为创作者的负累甚至反对者。在通常情况下,一个能证明女人真正存在的故事也更容易成为这个人的反对者。
或许,接着上面,我能回到我想谈而没法谈的问题:在现代,一个女人当然可以讲她自己的故事,但是,她有多大的勇气能承担讲一个故事的后果而不是在“逃避自由”中回到其他的异己的故事中?或者,因为成长的偶然性产生了太多的期待和不安,没有人能再回到别人的故事中——那将会产生进一步的不安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