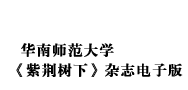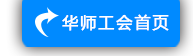夜舞的精灵——读《夜舞——西尔维娅·普拉斯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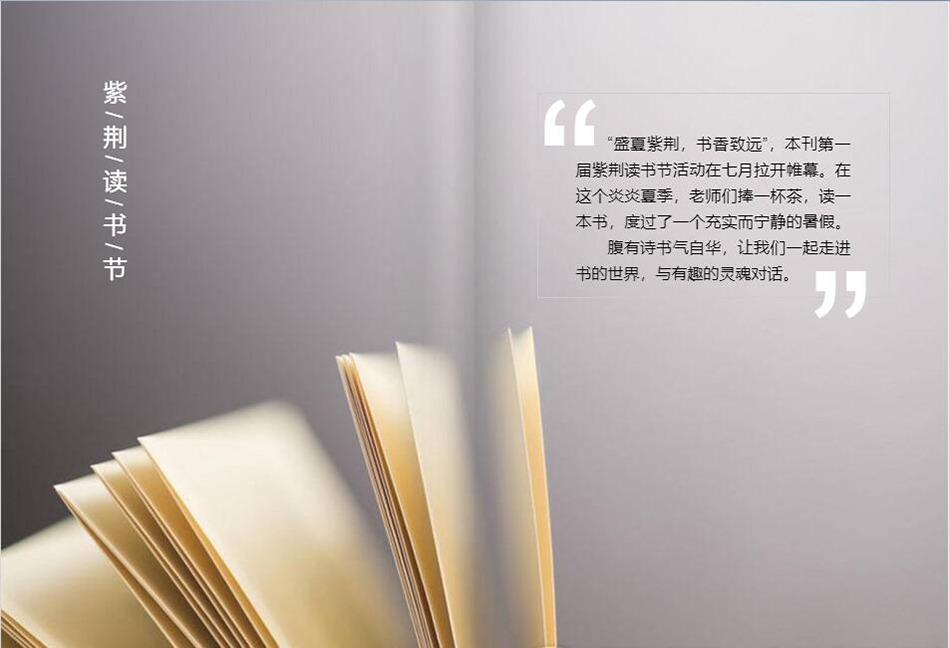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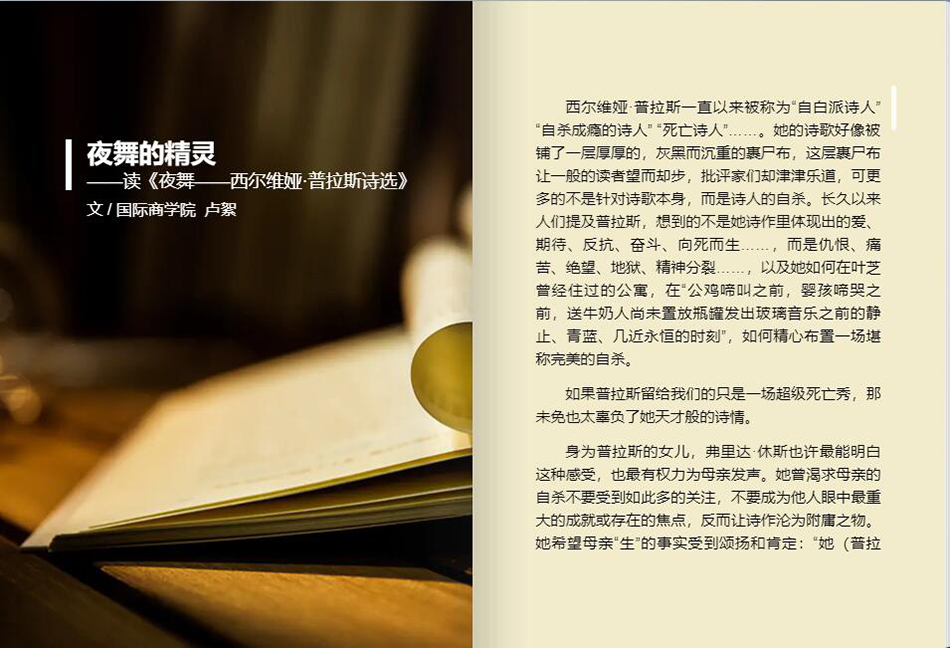
西尔维娅·普拉斯一直以来被称为“自白派诗人”“自杀成瘾的诗人”“死亡诗人”……。她的诗歌好像被铺了一层厚厚的,灰黑而沉重的裹尸布,这层裹尸布让一般的读者望而却步,批评家们却津津乐道,可更多的不是针对诗歌本身,而是诗人的自杀。长久以来人们提及普拉斯,想到的不是她诗作里体现出的爱、期待、反抗、奋斗、向死而生……,而是仇恨、痛苦、绝望、地狱、精神分裂……,以及她如何在叶芝曾经住过的公寓,在“公鸡啼叫之前,婴孩啼哭之前,送牛奶人尚未置放瓶罐发出玻璃音乐之前的静止、青蓝、几近永恒的时刻”,如何精心布置一场堪称完美的自杀。
如果普拉斯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场超级死亡秀,那未免也太辜负了她天才般的诗情。
身为普拉斯的女儿,弗里达·休斯也许最能明白这种感受,也最有权力为母亲发声。她曾渴求母亲的自杀不要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不要成为他人眼中最重大的成就或存在的焦点,反而让诗作沦为附庸之物。她希望母亲“生”的事实受到颂扬和肯定:“她(普拉斯)曾经存在,曾经竭尽所能地生活,曾经快乐和悲伤,苦恼和狂喜……。”
实际上,普拉斯临死前正在整理的诗稿,取名为《爱丽尔》(Ariel,又译《精灵》),一定是别有深意的。无疑这本诗集对于普拉斯有特殊的含义,也最能代表她的诗歌风格。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普拉斯使用爱丽尔这一名称的用心。首先,爱丽尔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火与大气的精灵,被禁锢于荒岛之上,成为公爵的奴仆,后来依靠自身的力量,重获尊严和自由;爱丽尔也是普拉斯“特别喜爱的一匹马的名字”,《爱丽尔》这首诗就是以普拉斯一次夜间骑马经历为基础进行的创作,骑在马背上,与奔腾的马合二为一,普拉斯一定品尝到了完全自由的滋味;同时,爱丽尔是基督《圣经·旧约》中耶路撒冷的别称,意为“上帝之狮”,是力量与权威的象征。谁又能说这不是普拉斯心驰神往的一个身份?
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的女性,一方面,传统的思想时刻约束着她们,要求她们成为贤妻良母、家庭主妇,没有独立的可能,谈不上尊严与自由。另一方面,时代在进步,在召唤作为知识女性的普拉斯走出家门,摆脱作为男性的附属身份,为自己发声,做一个真正自由的独立的人。同当时绝大多数美国妇女一样,普拉斯的短暂的一生都在为做一个“妻子”(传统女性),还是做一个“诗人”(现代女性)而矛盾、焦虑。普拉斯的丈夫,同为诗人且名声要高于她的泰德·休斯曾说:“普拉斯嫉妒男人过双重生活的自由:既有事业又有性和家庭生活。她忘不了这种嫉妒,它潜伏在心灵中,充满恶意。”且不说是否有恶意,但普拉斯深知自己的天赋和才情,她终究不会甘心做一个泰德·休斯背后温柔的妻子,永远生活在丈夫的光环下。
“我的头是日本纸做的
月亮,我黄金锤炼的皮肤
无限精美,无限昂贵。
别让我的高温吓着你。还有我的光芒。
独自一人,我是一朵巨大的山茶花,
红润鲜艳,开开合合,迸发出重重光彩。
——《高烧一百零三华氏度》
“我将成为墙壁和屋顶,保护着。
我将成为善良的天空和山峦,啊,让我成为吧!
一种力量在我身上增长,古老的坚韧。”
……
我是一条奶河。
我是一座温暖的山。
——《三个女人》
这就是普拉斯心目中理想、完美的女性形象,也是她希望成为的人。“我”纯洁如水晶,如婴儿,“我”是天使、是童贞女,“我”的身体美轮美奂,“我”散发着五彩的光芒, “我是雪白的胜利女神”,“我”是高贵仁慈的“戈黛娃”……。实际上,只要我们细细找寻,普拉斯在她的诗歌里塑造了许多完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充满神奇的生育能力,善良、坚韧,具有保护自身和他人的伟大力量。但是,她们却在男权社会中受着重重的压迫,包括精神与肉体。作为女诗人的普拉斯,她敏感而细腻地体会到了这些痛苦,当然也通过自身经验,通过诗歌表达了冲破传统束缚,找寻真实自我,实现女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它们认为死也值得,但我
要找回一个自我,一个女王。
她死了,还是在沉睡?
她上哪儿去了?
拖着它的狮红色身躯,玻璃似的翅膀。”
——《蜂螫》
“蜜蜂都是女性,
女仆们和修长的皇家贵妇。
她们摆脱了男人。
那迟钝、笨拙的结巴们,莽汉们。”
——《过冬》
“多久我能成为一堵墙,挡住风?
多久我能
用手的阴影使太阳柔和?”
拦截冷冷月光的蓝色弩箭?
……
我重新找到自我。我不是影子,
尽管有个影子跟着双脚。”
——《三个女人》
“我要成为我自己的女王”——这句话即便放到今天,也是非常前卫的。而当时的美国社会远没有今天那么开放,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方兴未艾,先知先觉的普拉斯们知道光明就在眼前,但她们处于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中。普拉斯心中的理想和现实距离如此遥远,可以想象她内心痛苦有多么巨大。《过冬》是普拉斯所写的“蜜蜂组诗”之一,写于普拉斯与丈夫分居后不久。在得知丈夫背叛婚姻之后,普拉斯主动提出分居,丈夫等于被赶出了家门。有趣的是,蜜蜂社会是以雌性蜂王为主导的社会,工蜂同样是雌性,而雄蜂在完成交尾任务后往往也会被赶出蜂巢。此时的普拉斯一定希望自己就如一只蜂王,能以摆脱雄性的控制而自豪。《三个女人》里的家庭主妇始终成熟、勇敢,她希望自己有超凡的能力,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能找回自我,不再充当男人的影子。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性的才华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被视为异类,天赋如此之高的普拉斯怎可屈服于任何男性,包括她死去的“爹爹”,包括她诗中反复出现的“黑衣人”、“法西斯纳粹”、“申请者”……。
阿瑟·欧伯格曾指出:“普拉斯的全部诗作表现了两种主要的运动——创造爱的运动和超越爱的运动。”普拉斯不是不爱自己,不爱这个世界,而是太爱了,心中火热的情感不容被现实的冷漠浇灭。她说:“对我来说,我们时代真正的问题是任何时代的问题——爱的伤害和离异。”因此,她要在诗歌中高唱爱的赞歌,生命的赞歌。诗稿《爱丽尔》的第一首《晨歌》便以“爱”开始,“爱发动你,像胖乎乎的金表……”,描述女儿弗里达的降生,“你毫无掩饰地啼哭/ 进入世间万物”,生命的开端,一切多么美好。《夜舞》中的儿子似“轻微呼吸的礼物,湿透的草地/ 散发你睡梦的芳香,百合,百合。”作为纯洁与爱的象征,普拉斯把儿子比作百合再合适不过。《你是》中的孩子活泼可爱,快乐纯洁:“小丑般,用手撑地乐翻了天,脚朝星星,有月亮脑壳……蹦跶如墨西哥跳豆。”在《尼克与烛台》中普拉斯满含深情地写道:“亲爱的,亲爱的,/我已在我们洞穴挂上玫瑰,/ 和温柔的毯子——/……你是马厩里的婴儿。”孩子身旁的普拉斯一定是温柔慈爱的,如圣母玛利亚散发着爱的光芒,她的孩子便如耶稣降临人世。普拉斯在对此诗的注解是:一位母亲在烛火旁照顾她的婴儿,她在他的身上找到一种美,那或许无法隔绝俗世之烦扰,对她却具有救赎的力量。
泰德·休斯曾说:“普拉斯最怕的就是失去她所具有的爱的天赋,没有人比她更爱生活,更有获得幸福的能力。”可她不善于驾驭它:它控制了她。当这份炽烈的爱无处释放、无法控制时,普拉斯便化身扑火的飞蛾,宁愿以死来护卫这份爱的纯洁与神圣。
“而我
是箭头,
是露珠,飞
自杀性的,与冲动合而为一
撞进血红的
眼,那早晨的大气锅。”
——《爱丽尔》
普拉斯纵马驰骋,想要冲破这郁积的黑暗,与她的爱马——爱丽尔合二为一,跨过脚下的岩石,奔向远方,去迎接黎明的到来。如一位出征的骑士,她勇敢、斗志昂扬、视死如归。生命就像飞驰的箭头,就像在血红的太阳下蒸发不见的露珠,让我们双手拥抱死亡又如何?死亡在普拉斯看来并不是可怕之事,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是再生必不可少的一步。《拉撒路夫人》便是借助圣经故事里的人物,讲述死而复生的故事。“……我披着红头发/从灰烬里起身, / 我吃人如吃空气。”《高烧一百零三华氏度》里生病的普拉斯似乎在地狱里走了一趟,她瞧见了“地狱的舌头”,最后在玫瑰花的簇拥下,在天使的守护下升入了天堂。“我想我正在上升/我想我会升起——/滚烫的金属珠飞翔……——升向天堂。”“再生”无疑是普拉斯诗歌中永恒的主题,就如死亡一样,因为在普拉斯的神话里,死——生是一对孪生姐妹,没有死亡就不会得到灵魂的洗礼,精神的再生。就如普拉斯自己所说:“拉撒路夫人有伟大的、可怕的再生天赋,唯一麻烦的是:她必须先死。她是不死鸟,是自由意志的灵魂……”
让我们回到《夜舞》,普拉斯一定也随着她的孩子在夜间尽情舞蹈吧!
“如此单纯的跳跃、盘旋——
无疑它们永远
漫游世界,我绝不会
坐着失去美……”
如一位降落人间的诗歌精灵,普拉斯披着华美的舞衣,这舞衣由奇妙的语言、独特的意象、神话、幻想和丰富激越的爱编织而成。她挥动着双臂,金发垂落,目光深邃,在黎明与黑夜尚未交接的最黑暗的时刻,翩翩起舞,缓缓上升——她最终成为了自己心中渴望的永恒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