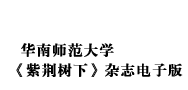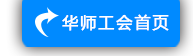女作家的颜值


《简·爱》有一段经典女性告白:“你以为,我因为穷,低微,矮小,不美,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和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貌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
这段独白真正表达了女性对于爱与尊严的理解,同时也是平凡女性超越世俗束缚追求精神平等的宣言。只是,常常是这样,理念是明晰的,意志也是强大的,但,在主流的审美之下,在社会约定俗成规则之中,对于外表不尽人意的女性,恼人的自卑和怯懦总是像小虫子一样,让情绪烦躁,让心情焦虑不安。
“有时候,我为自己没有长得漂亮些而感到遗憾,有时巴不得自己有红润的双颊、挺直的鼻子和樱桃般的小口。我希望自己修长、端庄、身材匀称。我觉得很不幸,长得这么小,这么苍白,五官那么不端正而又那么显眼。”可能,粗心的读者不会相信,这是简.爱坦诚面对相貌时的想法,她内心还是在乎自己的外貌的,因此陷入无端的烦恼之中。当罗切斯特对她说:“在我眼里,你是个美人,一位心向往之的美人——娇美而空灵”,简.爱竟然认为罗切斯特是在取笑她,她因为过度敏感而有些刻薄,她说:“你的意思是瘦小而无足轻重吧。你在做梦呢,先生——不然就是有意取笑,看在老天爷份上,别挖苦人了!”你看,坚定倔强如简.爱,其实也没有完全摆脱容貌平凡带来的自卑心理,而这也可以看作夏洛蒂.勃朗特本人对于外表的重视和芥蒂。
当然,以不好看又贫穷的女性形象为主人公,这是夏洛蒂想要颠覆传统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野心。只是,她一方面让简.爱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反抗现实,另外一方面她却无法摆脱那些如小虫子般的自卑,时时刻刻地跳出来,让笔下的简.爱也处于这种心理的折磨和挣扎之中。
伍尔芙曾经在文章里明确表示过她对于那段经典告白的反感,她认为“这种质问是疾风骤雨式的,对于生活过分的反抗,乃至成了一种病态的偏激。”她在文章后面对此做了解释,意思是她认为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里放置的自我太多了,写的都是“我爱,我恨,我在受苦!”“我爱”固然是和爱情和尊严紧密相关,而“我恨”想必其中有一部分确实是和没有美貌和财富带来的困扰有关吧。
现实之中的夏洛蒂本人,只是在人生最后两年享受了平和的婚姻。她曾有过一段世人皆知的卑微爱情。她给爱人写了那么多信,也没有得到回复,她自卑而绝望,她说:“先生,穷人不需要很多东西来维持活命,他们只要求得到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一点面包屑。可是如果拒绝给他们这些面包屑,他们就会饿死。”她如此卑微,一方面为自己爱上有妇之夫悲观绝望,另外一方面,多少也会因为外貌不够美丽不被看见而黯然神伤吧。
维多利亚时代,阶级成分和家族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夏洛蒂写出如此具有反抗精神的简.爱,让她努力反抗阶层、财富和性别歧视,至今都有其意义。但故事的结尾,不得不说,这种反抗有了别样滋味。看似简.爱带着尊严回到罗切斯特身边,但这个时候,罗切斯特双目失明,财产也不再丰厚,上帝剥夺了他的容貌和财富,夏洛蒂才让两人平等地在一起,实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门当户对。
同样在维多利亚时代,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她的名字叫乔治·艾略特。她比夏洛蒂.勃朗特的境遇要更为尴尬。乔治?艾略特喜欢哲学家家赫伯特·斯宾塞,给他写过情书,斯宾塞却因为艾略特的外貌拒绝了她。虽然他仰慕艾略特的才华,却声称艾略特远近闻名的丑陋致使自己难以对她产生感情,他不可能对她“粗壮的下颚、大大的嘴巴和鼻子视而不见”,“缺乏身体的吸引力这一点是致命的”。在斯宾塞的眼里,艾略特是长着一张马脸的蓝袜子。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宾塞认为艾略特之所以长成这个样子,因为她像男人那样思考,所以外貌也有了男子样。这样的说法,不仅仅是在打击艾略特一个人,其实还侮辱所有的女性,在他眼里,拥有理性和智慧的女性是丑陋的,只有拥有男性审美标准的颜值的女性才是美的。
“颜值即正义”,上帝没有赋予美貌和财富,意味着也就没有赋予公平。无论是哪个时代,斯宾塞对于艾略特的容貌打击,男性对于女性颜值的挑剔和苛刻,一直就没停止过。
八零后作家蒋方舟有一篇名为《我的相亲史》的文章,里面谈到有一位青年书法家。蒋方舟说:“那时我还没恋爱过,非常急于摆脱母胎单身,友人要介绍一个青年书法家给我,相亲的意愿传递给对方之后,他发了一条微博:‘一友人为我介绍@蒋方舟做女友,遂上网求图,看后大惊。如此之丑怎可做我女友,拒之。’书法家专门把这条微博@了我,大概是希望我反思一下。”还没等见面就拒绝蒋方舟已经够肤浅无知,但这还不够,还特地在微博上通知了她本人。这个做法,放在个人,有失风度,上升到性别角度,可以说以降低男性的智商为代价,用男性审美标准愚蠢而野蛮地打击女性。
还有比这更不堪的。作家虹影的新小说《绿袖子》在上海研讨会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鸿生如是说:参加女作家的讨论会每次都感到心情很矛盾,说实在的,中国50年代的女作家现在已经苍老不堪,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毕淑敏吓了一跳,十几年过去,她成了老太太了。60年代出生的我认识的,如林白、海男、陈染,仔细一打量,我觉得很残酷,她们已经基本上被耗尽、吞噬。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些作者说一些批评的话就觉得非常不忍,但是如果说一些捧场的话,我觉得又很没有意思……
从相貌到年龄,从青年书法家到中年教授,女作家们的才华没有被看到,但外貌却成了众矢之的,颜值成为了男权正义之后,也成为了性别原罪。
多益网络CEO徐宥箴曾经说过,女权只是丑女迫害美女的东西。他这个说法,确实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女权主义抨击了“美国小姐”选美活动。她们认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落入男性审美标准的陷阱,无时不刻在暗自选美,由此陷入内心恐惧。因为媒体对于女性主义运动的某些策略的夸大渲染,女权主义也不断被污名化,被某些人认为是丑陋的和失败的女性对真美女充满妒忌的主张和行为。这实在是有着险恶用心的思想,旨在将性别矛盾转化为女性内部斗争,削弱女权运动的影响和作用。
所以,当我在凤凰卫视看到余秀华的一段视频时,我突然想起了这个观点。
当时,余秀华在节目中谈的正好是女权。舞台上李银河、刘晓庆、徐晓楠等围坐一圈,余秀华则坐在这个圈子的对面。那一刻我的感触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余秀华的倔强和认真确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美,但另一方面,你会看到这种美有其挣扎的特质。舞台之上,负责感动的是健康美丽的人,围成一团,负责勇敢的则是与之相对的是一个残疾普通的人,如此充满鲜明对比的舞台场面,极具讽刺性地构成了关于残酷现实的投射:一个残疾的底层的不好看的女性注定是边缘的孤单的痛苦的,甚至是对立的。
这个时候,凝视余秀华的目光很复杂,有俯瞰习惯的男性目光,也有怀疑揣测的女性目光,坐在其中的余秀华,她的表情有多倔强,她的挣扎也有多激烈。她只能代表少数人,她的挣扎也只会是永远与主流审美之外的相貌一般的残疾的少数人的挣扎,她们注定要用更多的勇气和真诚去获得这个功利世界的认可,也获得无数鄙视链中密不透风的轻视和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