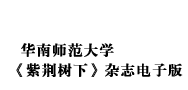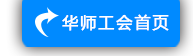皮相正义有多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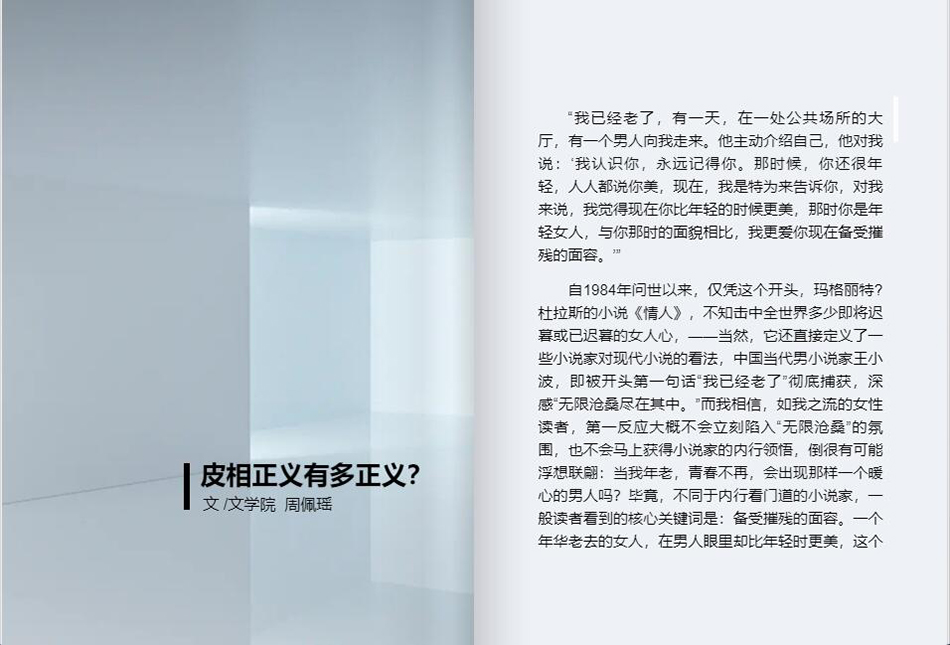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自1984年问世以来,仅凭这个开头,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不知击中全世界多少即将迟暮或已迟暮的女人心,——当然,它还直接定义了一些小说家对现代小说的看法,中国当代男小说家王小波,即被开头第一句话“我已经老了”彻底捕获,深感“无限沧桑尽在其中。”而我相信,如我之流的女性读者,第一反应大概不会立刻陷入“无限沧桑”的氛围,也不会马上获得小说家的内行领悟,倒很有可能浮想联翩:当我年老,青春不再,会出现那样一个暖心的男人吗?毕竟,不同于内行看门道的小说家,一般读者看到的核心关键词是:备受摧残的面容。一个年华老去的女人,在男人眼里却比年轻时更美,这个形象,不仅令作者杜拉斯“感到心醉神迷”,肯定也令无数杜拉斯的同性读者心醉神迷;——女人的美,或者说人的美,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被凝视才能获得确认。
这话若出自喜欢女人的男作家之口,在当下语境中,估计颇能激发一些野生女权主义者的键盘战斗欲望;身为喜欢男人的女作家,杜拉斯所言,如按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大概也难逃物化女性的嫌疑。不幸的是,在杜拉斯之前,早有现代男小说家清醒地指出人类认知的悖谬:以貌取人竟是人类视为理所当然的正义。
人的本质,取决于外表,还是取决于灵魂?灵魂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外表与灵魂的相关程度如何衡量?这是古老的问题,应该也是每个人在人生某个阶段难免悄咪咪扪心自问的困惑。
一辈子未能摆脱外貌焦虑的英国毒舌作家萨默斯特·毛姆,在七十岁高龄时仍执着于这问题:“身体的偶发事故会影响灵魂的‘体质’,我觉得这一想法会令很多人却步。但我本人对此笃信不疑。如果我不结巴或者能高上四五英寸,我的灵魂将颇为不同。”他深信,如果他的外貌是另一副样子,“我那些同伴对我的反应也就会不同,因之,我的性情、我对他们的态度也会两样。”其时他已走过大半个地球,靠自己的写作实现财富自由,拥有世俗意义的丰沛名利;而这个七十岁的老男人,还汲汲于外貌与灵魂的神秘关联,未能挣脱皮相的牢笼。
毛姆如此,每个社会人,大概也都如此,区别只在于程度深浅和敢不敢承认而已。然而,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个人自我形象的构建,总关联着一个或隐或现的他者,他人即镜子,无论男女,都无法彻底打碎这面他人之镜。尤其在遭遇“身体的偶发事故”时,他人之镜的魔力,甚至可以达到压迫性以至毁灭性的结果。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患了乳腺癌后积极寻求治疗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令她震惊的问题,对癌症病人而言,最大的痛苦和恐惧常常不是来自疾病本身,而是来自得病后他人的偏见和歧视,一旦你得了绝症,在那些暂时健康着的人眼里就成了异类。她由此写下了著名的长文《疾病的隐喻》,揭示人类关于身体的偏见是如何炼成的,文学在其中竟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人类的身体,从来不是一种客观的物理性存在,而是包含形形色色的主观隐喻。文学发现了这一奥秘,并利用着这一奥秘,一切“身体的偶发事故”,太适合于探讨人类自我认知的复杂幽暗了。
“一天清晨,格雷戈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
卡夫卡以如此简单平常的句子,开始叙述一个身体变形的重大事故,不带任何感情,自然产生不了任何杜拉斯式的沧桑感,他所要走的是另一条路。
与肉眼不可见的癌症细胞相比,一个人突然变成一只虫子,这得算是性质极其恐怖的身体偶发事故了。令人惊讶的是,变成虫子的格雷戈尔本人一点都不惊讶,确认了是在自己的房间后,他打算“再继续睡一会”,没发出任何惊慌的尖叫和恐惧的求救,平静得仿佛他生来就是一只虫子的外形;他作为人的自我意识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可怜的读者,很快就要从惊讶而沦入困惑了:那么,格雷戈尔是一只虫,还是一个人?当然,这个问题首先砸向格雷戈尔的家人,悬在他的父母和妹妹头顶之上,发出无声的拷问,接着波及他周边相关的有限几个旁人。旁人的反应没有任何悬念,完全遵守所见即所是的原则,他们看到的是一只大甲虫,而不是一个人;家人则陷于疑惑不安。
作为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支柱,格雷戈尔无比厌恶旅行推销员这个“多么累人的职业”,但为了替父母还债,为了让他深爱的家人过上安稳的生活,他不得不“日复一日奔波于旅途之中”,发现自己变成一只无法翻身的大甲虫后,他还担心:“我的火车五点就要开了。”迟到的后果很严重,对此,他的家人和他一样清楚,当他还在床上时,他的三个家人分别从通往他房间的三个门敲门喊他——他的房间有三个门!这个空间状况,触目惊心,直接从视觉上呈现了家人与他的关系,纳博科夫在他的《文学讲稿》中画出了萨姆沙公寓的布局草图,断定“格里戈尔的家庭成员都是附在他身上的寄生虫,剥削他,从里到外蛀食他。”同为小说家,纳博科夫深谙《变形记》空间叙事的功能,由此抻出小说的主题:究竟谁是虫?谁是人?
发现格雷戈尔的外形变成虫子后,母亲“晕倒在地”,“父亲充满敌意地握紧拳头”,妹妹怀着紧张忐忑的心情开始照顾他的饮食。变成甲虫的格雷戈尔不仅失去了人的形体,还失去了人的语言、人的饮食习惯,人的行动能力, 再不能出门为家人奔波挣钱了。他们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寄生生活,开始独立谋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惶惑,他们确认格雷戈尔已是虫子。最后由格雷戈尔心爱的妹妹在一个夜晚做出宣判:得设法弄走这怪物,人和这样一只动物是不可能共同生活的。悬在家人头上的那把剑,准确落在格雷戈尔头上。身体状况已多灾多难的他,始终没有失去人的意识和情感,被家人宣判为怪物、动物之后,他一心想赶快爬回自己的房间,在黑暗中,“他满怀感动和爱意地回想着家人。他认为自己该消失,这想法很可能比妹妹还坚决。”当钟楼的钟敲响三下,格雷戈尔在“茫然而平静的沉思之中……无力地呼出最后一口气。”
直到临死前的最后一刻,格雷戈尔都不曾怀疑自己是格雷戈尔,是个人,可他清清楚楚听见妹妹对父亲说:“你只要设法不去想它是格雷戈尔,我们一直相信它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幸。” 家人决定摆脱他们的不幸,这铸定了格雷戈尔真正的不幸,如家人所愿,格雷戈尔死掉了。小说的噩梦气氛至此达到顶点,死去的究竟是名为格雷戈尔的一个人,还是一只没有名字的怪物?在家人眼里,死去的是“它”,是一个不能与人类共存的“怪物”;文本的人称指认却始终是“格雷戈尔”、“他”。卡夫卡的答案如此分明:死去的是一个人,而非一只虫子、一个它。他死于家人的非人指认,最亲近的人,是最清晰的他人之镜,能呈现最彻底的绝望——它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彻底碾碎了格雷戈尔作为人的信念。
卡夫卡的小说,按米兰·昆德拉的说法,探寻的是人存在的本质。那么问题来了:人如何确认自身存在的本质?
卡夫卡所要讲述的不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而是一个荒诞而恐怖的启示,细思极恐的那种。
小说开头,格雷戈尔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壳虫,没感到惶恐,因为他仍以人自我意识,而他的硬甲不过是他“在背叛、冷酷和肮脏的现实中寻求保护的迫切需求”。当一个人的外表与自己的内心需求自洽时,人不会对自己的外表感到不满或惊讶。格雷戈尔对自己的虫子外表安之若素,直到迎来妹妹对他的决定性判决,宣告他坚硬甲壳的保护功能彻底失效,他毫不犹豫做出了与《判决》的主人公格奥尔格同样的决定:怀着对家人无言的爱,如家人所愿结束自己的生命。
格雷戈尔死后,小说明确交代了季节:“现在已是三月了”。格雷戈尔的父亲赶走了家里的三个房客,一家三人决定坐电车去郊区玩。(纳博科夫注意到了三这个数字在小说中的“技术意义”,指出“那是三月底,正是昆虫从冬眠中醒来开始活动的时候。”)小说结束于:“电车到达目的地时,他们的女儿第一个站起来,伸伸她年轻的身体。在他们眼中,这恰是对他们新的梦想和良好心愿的一种肯定。”纳博科夫认为这结尾“就其讽刺性的简洁来说是最精彩的。”原因在于:“格雷戈尔是在虫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他的家庭成员则是装扮成人的虫。格雷戈尔一死,他们虫的灵魂突然意识到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了。”
小说家纳博科夫眼里看到的是精彩的讽刺,而经他提点,从“伸伸她年轻的身体”这一动作和三月这个时节,我感到的是凛冽的恐惧:那动作是一条刚从土里钻出来的虫子呐!她父母看她是个人,周围人看她当然也是个人。每个人都活在他人眼里,可人的灵魂能被他人真正看见么?
卡夫卡把问题和恐惧一并留给了读者:人存在的本质是孤独无依么?如果没有一个哪怕是不可靠的支点,人何以承受这巨大的孤独?
一个人能与人无涉、彻底独立地举起自己的灵魂吗,就像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
“我是谁?”与他人眼里的“我”,重重叠叠,相互缠绕,彼此渗透,卡夫卡穿越重重幻影,找到了世界的坚硬冷漠和个人的孤独脆弱,多么令人绝望!
而鲁迅会引他所欣赏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声明“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而“身外”即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洞察了虚妄之实有,大概也就获得了承受孤独的支点,无论心怀什么样的利器,人终究要活在人间,看人,被人看,走着瞧又何妨。
参考书目: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王道乾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
萨默斯特·毛姆《作家笔记》,陈德志, 陈星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 中短篇小说》,谢莹莹等 译,作家出版社,2011年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
鲁迅《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