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雅致的生活——读梁实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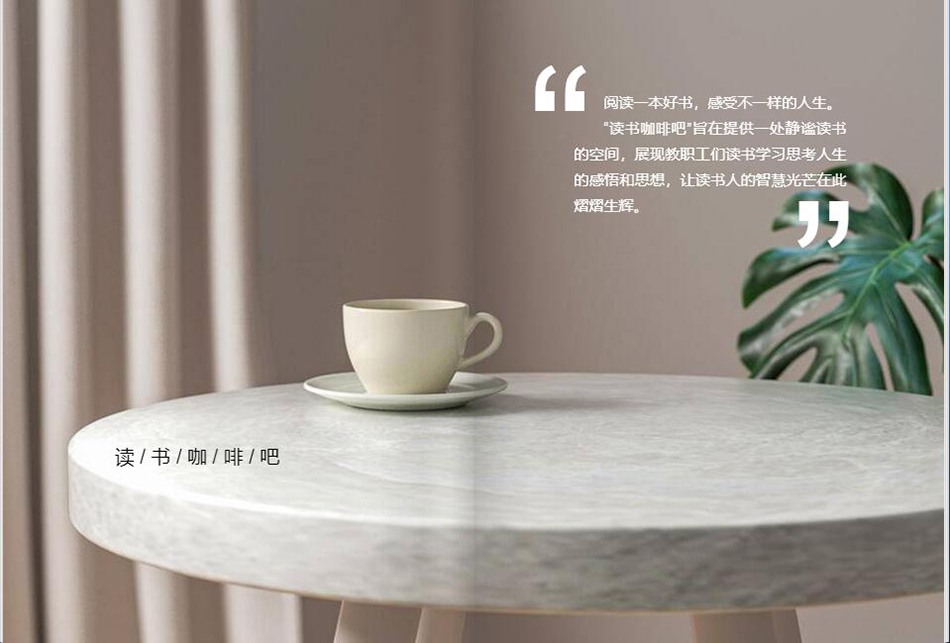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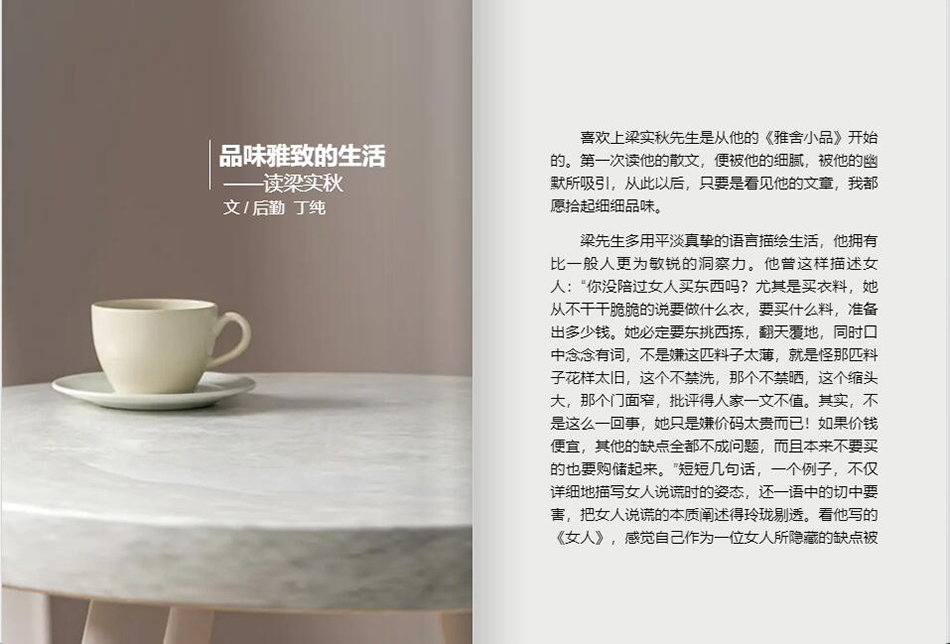
喜欢上梁实秋先生是从他的《雅舍小品》开始的。第一次读他的散文,便被他的细腻,被他的幽默所吸引,从此以后,只要是看见他的文章,我都愿拾起细细品味。
梁先生多用平淡真挚的语言描绘生活,他拥有比一般人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他曾这样描述女人:“你没陪过女人买东西吗?尤其是买衣料,她从不干干脆脆的说要做什么衣,要买什么料,准备出多少钱。她必定要东挑西拣,翻天覆地,同时口中念念有词,不是嫌这匹料子太薄,就是怪那匹料子花样太旧,这个不禁洗,那个不禁晒,这个缩头大,那个门面窄,批评得人家一文不值。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只是嫌价码太贵而已!如果价钱便宜,其他的缺点全都不成问题,而且本来不要买的也要购储起来。”短短几句话,一个例子,不仅详细地描写女人说谎时的姿态,还一语中的切中要害,把女人说谎的本质阐述得玲珑剔透。看他写的《女人》,感觉自己作为一位女人所隐藏的缺点被一览无遗无地自容,却还被其敏锐的观察力深深所折服。
读梁先生的文字,你能感受到他那种柔情似水的温柔。在他细腻的笔下,仿佛一切景语皆情语。因此你读他文章能感受到他的雅致、风趣,再多的忧虑在此也会烟消云散。梁父颇擅苦中寻乐,在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中,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梁父居住在一座“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但他仍饶有情趣,名之为“雅舍”。“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尽管雅舍简陋,不蔽风雨,水滴风刮乃是常事,但在他看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梁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在我们看来,分明是偏僻荒凉的荒郊野外,他却仍能从中觅出滋味。“若说地点荒凉,则月明之夕,或风雪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见情谊。”在梁父笔下,向来被唾弃山高路远的瓦屋茅舍,居然成为你我人缘亲疏的试金石,好有一番风味。我不曾居住过乡下,但自小厌恶回乡,因为我印象中的乡下总有泥泞的小路,崎岖的山峰,肮脏的瓦房,聒噪的蚊虫,简陋的茅房,就连想“方便”一下也颇不方便。这些“不堪”,梁父在雅舍也同样面临过,但他一改不悦的心态,仍泰然处之。
梁先生除了在品世、品人、谈吃等方面以轻松幽默的笔吻向我们娓娓叙说他数十年的阅历,一生还致力于研究莎士比亚,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将《莎士比亚全集》译成中文。然而对于他这三十年的成果,他却戏谑道:“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没有学问,如有学问;二是必须不是天才;三是必须活得相当久。庆幸这三个条件都具备,才得以完成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梁父的幽默和谦逊,让我不得不佩服。
然而,提起梁先生,难免会有人提起鲁迅先生曾自杂文中命其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或许在鲁迅先生看在,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人民都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他写的散文过于小资,有些许帮闲的嫌疑。未曾了解梁父伊始,我也一度以为他便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但在拜读过他的文章,了解过他的生活背景后,我想我是能够并且愿意理解他的。
梁先生自幼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虽然比不上贾府,但也算个中产阶级,无虑生计。因此面对民族的痼疾,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同于鲁迅先生为国难而四处奔走疾呼,却也同样寻找着一种救国救民方案。在当时的中国,关于“抗战”的文章有许多,而梁先生则是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他认为文学的创作并不需要服务于抗战,写作材料并不一定要局限于“抗战有关的”。他在《编者的话》曾道:“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答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是梁父在重庆担任担负报馆副刊时选择稿件的标准,
从他的要求看来,我们可知,他并没有逃避抗战题材,也不是无视民族危难,他只是追求文学的独立性,强调文学的作用。纵观他在抗战时期写下的文章,我反而会感叹,他是如何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下把中国的一些人文、山水、风月、器物描写得如此有韵味,想必他内心一定是有坚定的信念和从容的生活态度吧!况且,在当时,能够引起鲁迅先生的注意,并且与其进行多番论战的人,文采和胆识也肯定非属常人了。或许梁先生主张的闲适笔调无法直接拯救当时的中国,但是他幽默风趣的文字背后,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深厚文学底蕴。
不写“与抗战有关”的文章并不影响梁先生对中国的情感。梁先生原决定与定居美国的女儿同住在美国,却在申请美国国籍时选择了放弃,他说:“入美国国籍必须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祖国。”还有人问他人生的遗憾是什么,他大概列下了四类,其中一个便是: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死前也有同感。梁先生这种坚贞爱国的情怀,将他列为“资本家的走狗”也说不太过去。我想,他当初写闲适散文时也绝无此意,但与鲁迅先生进行多轮辩论战,大抵不过是文人的傲骨罢了。
斯人已去,而风采依旧。他柔情似水,以朴素的语言留下脍炙人口的作品;他坚贞不屈,以其忠贞的爱国情怀终能被世人所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