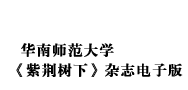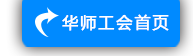大麦


昨晚,一个人在月下漫步,不远处的夏枯草挺着身子,叶子盈盈发亮。清新的味儿,突然使我想起故乡的大麦——大麦在月光下安静自若,颇有俗世的生活气息。
曾经,在江淮平原,大麦是小众的,像几辈子单传的小户人家。在人们看来,大麦虽然是老大,却没有弟弟小麦有出息,完全是小麦的陪衬。“大麦青青小麦黄”,之所以叫大麦,先于小麦成熟吧。大麦收完,天空响晴,布谷鸟叫了,“布谷布谷,割麦种豆”,收割的是小麦。至于大麦嘛,庶几无人提起。农人眼里,小麦是养家口粮,大麦是牲口饲料,诗人海子说:“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五月的风吹黄了麦子,也吹熟了农人的心,小麦囤在家里,麦子进家,心里不慌。小麦是贴心贴肺的,也可以说麦子是我们的心上人,秋季种麦子,农人费心将小麦地整饬得利利索索,盼得来年有个好收成。
而大麦呢,哪有这样的殊遇?大麦、小麦原本是一对兄弟,所享受的待遇却是霄壤之别。农人对大麦也没那么用心,耩完了麦子,想到还有些地荒着也是荒着,种大麦吧,就随便簸些种子,撒了、甚至肥料也省了,“没有花香,没有树高”,说的也是大麦。它爱长不长,才没人管它呢。
我印象中,大麦在我家乡叫做“料”——主要用来犒劳牲口的。农忙,人要吃好,牲口也要添膘。农人将大麦机成粉,均匀拌在草里——那是牲口难得的美味。俗话说,吃饱喝足了才能干活。农谚:“光干活,不给料吃。”指雇主为人吝啬,“胡萝卜加大棒”,只有大棒,没有胡萝卜了,那可不行。小麦放在囤里,里三层外三层裹实了,以防生虫、发霉;而大麦则装在蛇皮口袋里,松松垮垮的,早晚一天送进牲口的肚子里。
也不知何时,大麦走上了饭桌,成了保健食品。一些湘菜馆,把炒焦黄的大麦,泡了,香气宜人,喝一口唇齿留香。书上说:“大麦茶开胃,助消化,有助于减肥。”原来大麦茶还有此功能。我小时,母亲用大麦做炒面,将大麦面炒熟了,放入白糖,开水冲了,也算美味,只是一不小心会被呛着。
网上一度热传一首译诗《大麦歌》,李敖译的,也有人说是朱令的译文,诗的内容是这样的:“大麦俯身偃,既偃且复起,颠仆不能折,昂扬伤痛里。我生也柔弱,日夜逝如此,直把千古愁,化作临风曲。”看样子,柔弱的大麦骨子里是坚强不屈的,也是乐观的。普通人的命运不正如此吗?柔弱而又坚强,身处逆境而不甘堕落。读这首诗,想回到乡下,站在高岗上,远望无垠的田野,内心无比澄澈,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