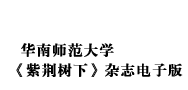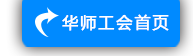“你就是你寻找的” ——关于逝去与重生的一片瞬间


在去科尔马的火车上,伊纳还是难以回过神来。夜班回家后,她觉得精神还好,做了一锅炖牛肉,想着送一些到女儿学校,算是弥补生日,还留了一份给玛内芮。牛肉还在锅里翻滚,电话铃响了起来,手忙脚乱还把洋葱汁溅到眼睛里了。
接完电话,她不得不用厚毛巾来应对大量涌出的眼泪,眼前雾影重重,对着水龙头冲洗整个脑袋,两分钟以后,清凉带走了眼泪以及眼泪在大脑中的源头,只剩下胸腔内部还在抽缩。关掉火炉,把没有做好的牛肉倒进垃圾桶,收拾好厨房,她来到卧室收拾自己。
换上一套黑色的礼服,又带上两套换洗衣服,检查家里水电,给女儿留纸条:“亲爱的茱莉亚,太奶奶有事找我回去,我去一趟科尔马,要下周末才能回来,你照顾好自己。爱你。”然后定定神,给主任电话,主任在那头还是担心:“请假没问题,你自己呢?确定可以吗?要么让茱莉亚这周末来我家,我太太很喜欢她。”于是她又在纸条上给茱莉亚留了主任的联系方式。
去火车站的路上,她买了硬面包,味道就像馕,就这么一直抱在怀里。邻座老人从书的上方打量她,这个面相年轻的中年女人自上车以后就一个姿势:抱着她的面包,眼睛几乎不眨地看着窗外。
到达科尔马的时候已经黑天了,伊纳抱着面包,打了一辆车,车程是半小时,终点是科尔马郊外的养老院。这所空旷而风景优美的养老院,平时访客也不多,当伊纳下车的时候,抬头就看到院长在正对大门口的窗前冲她挥手——距离她俩这通电话,刚过去五六个小时。
院长先带她去小教堂,外祖父乔伊斯的遗体,暂时安厝在小教堂的地下室,等她来了之后,明天就可以举行葬礼。守灵的嬷嬷递给她一根蜡烛,在圣母面前跪下,她不知道自己是要祈求还是应该哭泣,大脑是一片迟滞的灰白,胸腔里的抽缩蔓延到手指,需要两手捉牢,才能把蜡烛插到烛台。
“安娜应该是睡了。”她谢过院长,本想自己去看安娜,院长捂住她还在微微抽缩且冰冷的手:“我带你去吧。”她看一眼放在长凳上的面包,院长帮她拿上,一手牵着她,方便她用另一只手环抱着面包。
法国北部的月光显得格外清冷,这所建立于中世纪的砾石建筑,房间高大幽暗,今晚有护士一直陪着安娜,所以壁炉也点上了木柴。伊纳把面包温在壁炉灶上,脱下外套,轻轻躺在安娜身旁。
她用手遮住眼睛——今晚的月光无处不在,让肿胀的双眼更加干涩。“露西娅。”这个儿时的小名忽然冲出脑海、从她自己口中喊出,“露-西-娅-”每念一声,好像就能让从内到外的抽缩少一分。但是并没有,在抽搐一阵阵袭来的稠密关头,她侧身抱住外祖母的背,用嘴唇发声念着自己的小名,当祖母的体温环抱到怀里的刹那,滚烫的泪水喷涌而出。
乔伊斯的生前好友、方济各神父主持了他的葬礼,经过一整晚亮如白昼的月光普照,第二天是个无风的日子。铃兰和毛茛组成镶嵌宝石光斑的波斯地毯,铺满了教堂后小墓园的山坡。
伊纳用外祖父穷尽一生研究的波斯语,念诵了他所爱的鲁米的诗,低沉回旋的吟唱在无风亦无边的时空涯际飘逝:
“我的诗像埃及面包,
过了一夜就不能吃。
趁新鲜吃吧,在落满尘埃之前。”
“当你寻找宝石你就是宝石。
当你渴望面包你就是面包。
知道这个秘密很好:
你就是你寻找的。”
她怀中的面包,就是外祖父喜爱的波斯馕,此刻也捧在手中,随着泥土,向墓穴中洒落。
待墓土填平、墓碑立好,她仔细擦拭掉碑石上每一丝灰尘,然后继续吟唱:
“像一团云。
是哭泣的时候了。
像一座山。
是负重的时候了。”
院长帕里西嬷嬷抱住了安娜,安娜空洞的眼睛注视着伊纳,喃喃念道:“露西娅,不哭了……”这是她现在唯一能记得的名字。
伊纳稍微停顿,她答应过外祖父,一定要在最后的时刻,笑着大声吟诵这首关于爱的诗,“生命可以息止,但爱未曾离开。露西娅,你一定要相信。”
“当我心爱的人和我在一起我就谁也不怕。
我有一把剑。
不用害怕针。
我的嘴唇永不会干。
河流会来找我。
我的心永不会忧伤。
富有同情心的心爱的人和我在一起。
我沉溺在甜里。
对我来说不存在苦。
冬天不消耗我。
春天和我在一起。”
最后一句的明亮尾音,贯穿了头顶到天空的气息和光亮,一种强大的引力将她的大脑和意识抬升到高处,有什么东西被击落下来,但又并未留下尘埃、甚至些微痕迹。有窗口在内心敞开,但又并非由外力造就,而是尘埃散尽、阳光自内而外地找到自己的通道。最后一片泪水洗净了面颊,方济各神父看到,她渐渐明亮的脸庞、在泪中微笑,仿佛风雨过后的天空。
作别神父和嬷嬷,陪外祖母吃完午饭,伊纳就动身返回。玛德琳嬷嬷吻了吻她的额头:“孩子,你想回去就回去,这里有我们。”她回吻了嬷嬷的手,吻了安娜的面颊,然后在二人的注视下,坐上门口的汽车。蓝色太空旋转着亮黄的正午太阳,周围环抱的广大无边的葡萄园、阡陌相通的气流汇集旋转、朝向太阳飞升,绿色蓝色黄色的光芒四射,填充了伊纳的眼睛,由此贯注到喉间、心肺间,她大口呼吸着混合着新翻泥土和运河河水味道的空气,整个上半身就像鼓起的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