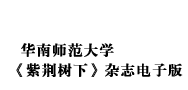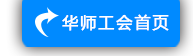“珍重”与“新生”——看《山河故人》和《狂野时代》


12月12日,贾樟柯的《山河故人》要重映,距离它初登银幕已整整十年;而就在12月初,我刚在影院里看完毕赣的《狂野时代》,迈出影院时,竟恍惚不知身在何处何时。这两位我格外欣赏的作者导演,创作路径看似南辕北辙,却都在长镜头、方言与空间中,为乡土与个体刻下了独一无二的精神印记。
长镜头
大学期间我初接触巴赞的电影理论,那时的观影经验不足以撑起我对长镜头的理解,直到《东京日和》和《乡愁》。近些年的长镜头佳作名单里,我又加进了阿方索的《罗马》和门德斯的《1917》。
说起贾樟柯的长镜头,它更像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充满了朝向底层的人文关怀。《小武》结尾处的长镜头中,小武被拷在电线杆上,景深里的小人物被盯着,满是荒诞悲凉;《三峡好人》船舱中,长镜头把看手相、闲唠嗑的普通人的细碎命运都装进了大的时代变革里;《站台》剧团排练的固定长镜头,落日旧楼混着落寞,把逝去时代的怅惘都揉进了纪实里。《山河故人》最动人的莫过于沈涛在雪地中独舞的长镜头:镜头从空荡的街巷缓缓推近,雪花落在她的发梢,叶倩文《珍重》的旋律从远处传来,她踩着迪斯科的节拍独自旋转,背景里的汾阳老房与远处的新楼形成新旧对照,青春的回望与故土的变迁都在镜头的流动中自然铺展,成为贾樟柯长镜头美学的经典。
相比之下,毕赣长镜头里的“时空连贯”常常挑战观众的耐性。《路边野餐》长镜头40分钟,《地球最后的夜晚》长镜头60分钟,《狂野时代》最后一个故事的长镜头30分钟,但它们不是记录和复刻现实,而是制造个体的精神迷宫。凯里的废旧钟表、旋转苹果,邰肇玫攥着的半块面包、蹭过蛛网缠满的手套,这些私人记忆的符号跟时代不再牵扯。毕赣擅长把长镜头变成精神容器,在本土语境里进行创造性转化,给华语艺术电影铺了条独一份的路。
方言
上世纪末的中国,华语影坛掀起了方言热潮。方言撕开了普通话一统银幕的单调,成了地域文化的发声器,但又被市场和文化裹挟,在滥用中变成刺向艺术的刀,例如《疯狂的石头》凑齐各地方言玩出喜剧狂欢,《让子弹飞》则专门推出方言版收割票房。
方言也成为导演个人风格的纹身,贾樟柯在方言里刻下现实,毕赣则纹出了诗意。《山河故人》里,贾樟柯把方言当脐带,拴着汾阳的土地和时代的阵痛,汾阳话、粤语、邯郸话、上海话、洋泾浜和英语,dialects may thrive but also be trapped(方言既可能繁荣,也可能陷入困境)。语言的纷杂象征着人在物质世界和文化场域的流动,但如何驻足,何以为继呢?
毕赣的贵州话则游荡在魔幻的雾里,凯里的街巷在方言里变成了记忆的迷宫,迷惑又迷人。《路边野餐》中陈升用凯里方言絮絮叨叨地念着诗,软糯的尾音极富质感,那些混杂着诊所气味与山路风尘的台词,让这个背负过往的中年男人在一方湿润的天地扎下了根,长出血肉。《狂野时代》的 “478”在贵州方言里谐音 “死去吧”,它悄悄串联起末日背景下的宿命感,又为吸血鬼的奇幻叙事平添了疏离感。
空间
歌舞厅是普通人生活最具生命力的空间之一,它让人物“活”起来。在时代拆和建的大背景下,让人物“沉”下去的则是废墟。
《山河故人》里,沈涛甩着头发跳迪斯科,晋生挤进来贴紧她的腰,梁子撞开门时,霓虹正好把三人的影子劈成碎块。每盏霓虹灯都闪着即将散场的信号。然后,晋生的钞票、梁子的拳头,都砸在迪厅的地板上,最后碎成梁子背走的包袱。2006 年,沈涛回到待拆迁的老院收拾物品,蹲在碎瓦堆里捡父亲的旧茶壶。墙身写着洇湿的 “拆” 字,断梁上还挂着旧窗帘,是她与晋生、梁子三人情感破裂的具象载体。2025年,镜头从澳洲沈涛的独居场景切回汾阳,老院已被拆成平地,仅余半堵墙立在荒草中。风卷塑料袋擦过砖缝,耳畔响起沈涛手机里循环的《珍重》。
《狂野时代》讲至最后一个故事,人类已经走到千禧年的转折处,在赛博朋克式的废墟里,迪斯科的节拍混着雨雾,点歌台依旧如火如荼。少女藏起吸血鬼的尖牙 —— 她是废墟里的 “活物”,也是记忆的幽灵。迷魂者化身为阿波罗,牵着少女的手跑过蛛网缠满的巷口,两人的喘息被长镜头揉进残垣的裂缝里。“为什么人类总是喜欢看太阳升起的那一刻?”因为人类需要在黑暗之后新的光里重启。少女用尖牙咬开阿波罗的脖颈,等待爱给予她的一线生机。
据说,《山河故人》还将在2035年举办20年重映仪式,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好的电影不仅仅闪烁地照亮影院120分钟,它还会让散场后的人们频频回望、回应和回响。十年前的《山河故人》以“珍重”叩问离别,如今的《狂野时代》以“新生”回应迷茫,而这些藏在镜头、语言与空间里的精神印记,正是华语电影最珍贵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