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不知身是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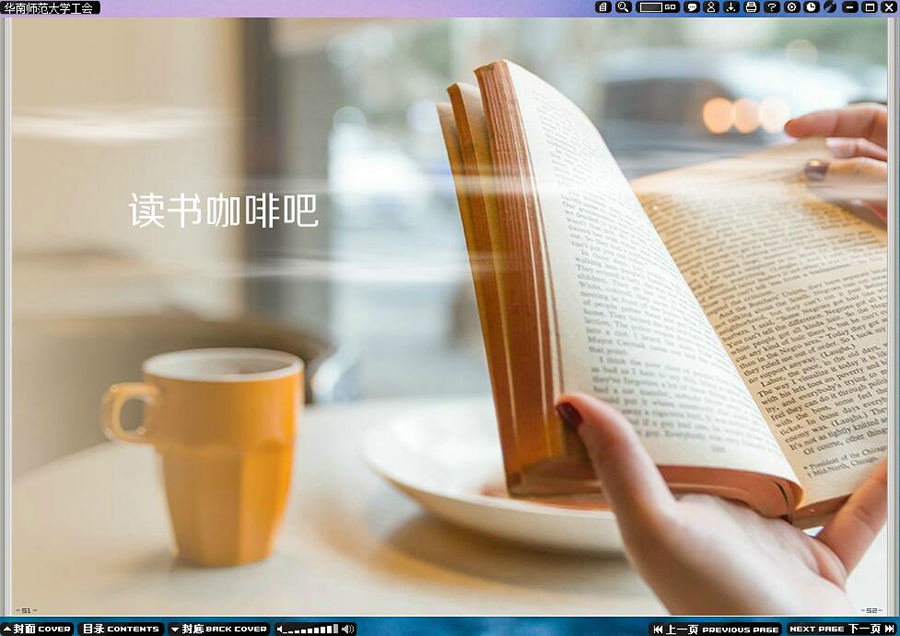

贾家遭逢变故以后,除了早逝的黛玉,其他一众痴儿怨女的下落如何了?宝钗独守空房?凤姐被休惨死?湘云被卖入娼门?还有其他的钟灵毓秀,她们都何去何从了呢?每个人都结局悲惨吗?前八十回越是光鲜,后四十回就越是凄凉。当大宅门雨打风吹去以后,公子小姐何去何从呢?没有了风花雪月,他们都风餐露宿吗?因为续作成疑,读者和红学家们只能从十二钗的判词以及各种评本里寻找蛛丝马迹,猜测可能性。在文学史上,贾家的家族史就像开创了一个文学母题,有关大家族的命运历史,被许多文学后辈所模仿、翻新。比如巴金的系列小说《家》《春》《秋》。
还有,叶广芩的《采桑子》。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采桑子》就像《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现代改写。把贾家存在的时间往后移数百年,到清末民初的时候。“贾”家虽然仍在“政老爹”手上,但是风雨如晦已经让根基隐隐倾颓,墙垣上也印下淡淡斑驳。清国已覆,岂有完卵?呼喇喇似大厦倾是迟早的事。
作者叶广芩本身即是贵族出身,满族,祖姓叶赫那拉。她的小说《采桑子》,写的是清末满族贵胄金家的家庭,以金家最小的女儿“我”的口吻,以全知视角来叙写金家各人的故事。金家一共十七口人,做镇国将军的阿玛和他的三个妻妾,以及十四个儿女。有人说,《采桑子》是叶广芩的自传体小说。这对创作者和具有基本文学常识的读者来说,拿小说对号入座是不专业、不成熟的。即使是遥远的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曾开宗明义: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因此,《采桑子》或许取材自叶广芩的亲身经历,“在适合的土壤和空气中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了我的作品”(《采桑子》后记),但不能说是作家的真实经历。那么为什么会认为这是作者在写亲身经历呢(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旧红学的索隐派一说),大概是因为小说所散发出来的“真”。真实可感,真情实感,这种“真”在《采桑子》里显得那么纯粹深厚,让人体会到,没有真实经历是带不出来这股“真”味、真情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读者坚信《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坚信曹公若没经历过那“一把辛酸泪”,是写不来那“满纸荒唐言”的。
《采桑子》是金家的故事,对金家的每一口人,甚至与金家有亲属关系的人均有涉及。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金家的每个成员各有小传,有长有短,有详有略,合成洋洋洒洒一部“金史”,也是八旗子弟在改朝换代以后的命运。他们的转变,从极盛到极衰;他们的个人经历,有荒唐的,有悲惨的,有辛酸的,有遗憾的……共同谱奏了一曲时代的遗音。
八十年代曾有“京味小说”一说,其中的代表作家邓友梅,在给《采桑子》作的序里评价旗人:“有文化没职业,有教养没技能;衣着寒酸举止高雅,手不能提却能写对联画画,肩不能挑却能拉山膀起霸。只可惜书画还不到卖钱水准,唱做仍停留在玩票阶段。他们对人有礼貌,说话有分寸,文墨有根底,举止有风度,穷愁潦倒却又目空一切,……坦白地说,论文化素质和礼节教养,旗人的平均水平比我们有数亿文盲的汉族高。他们缺乏谋生技能或命运坎坷不是个人智能、品行、性格造成的,而是因为从老皇上赏赐特权那天起就断了他们日后的生存之路。天下没有不换的朝代,也没有永存的特权!”多么深刻有见地的评断啊!邓友梅先生是真正看到了没落旗人的优缺点和无能为力。金家的故事既摹写昔日皇孙贵胄的高贵文雅和荒唐,又刻画末路贵族的凄凉与无奈。
这里只挑出金家成员其中的两个人:大姐金舜锦和五哥金舜锫的故事。为什么选他们俩人?因为在众多金家人中,舜锦和舜锫是真正的叛逆者。他们的反叛不是受到谁的引导,不是得自哪一方的启发,而是纯出于天性;他们的反叛不是要推翻封建传统,不是要追求个性,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自觉,他们也没有接触过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求。事实上,他们俩是彻底的封建家庭里的公子小姐。惟其如此,他们的逆反才爆发得更加惊心动魄。他们追求的,不过是最基本也是最纯粹的天性:自由。
大姐金舜锦是金家的第一个孩子,“是金氏一门的长女,自然得到全家人的惯纵,加之满族人家里最重的是女孩儿”,大格格的地位和风度都是无与伦比的。她就是那个时代那个家庭里最庄重最典型的代表:不怒自威,居高临下。虽然大格格如此飘逸绝俗,但她却有一个最接地气的爱好:唱戏。金家人都是戏迷、票友,但是唱得最好,在亲友间都有名声的却是大格格。大格格平日端庄自持,唯有求其开嗓唱戏,却是有求必应。“谁都知道,有事求大格格,十回有十回得碰钉子,唯独求她唱戏,十回有十回答应,从不推诿。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大格格才变得笑容可掬、平易近人,才成为她下面十几个兄弟姐妹的可亲的大姐。”然而这样地位高尚的大格格,她的婚姻却是十足封建的。她的婚事是金家舅老爷给包办的,未来的夫家是北平警察总署署长宋家。虽然宋署长夫妇粗俗野蛮,且又是汉人,“搁过去,皇家的格格怎能下嫁给一个汉人警察的儿子?”但时代不同了,现在这警察署长是权势人物,他的儿子留学德国,是北平德国医院的副院长。这样的家世很可以给金家大格格作配了。在两家见面之后,恰好逢上北平名媛义演。这次义演是大格格人生的高潮,同时也是她凄苦下场的序幕。
大格格在义演前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胡琴伴奏,有一天她未来的婆婆,特地找来一个在北平德国医院跑腿的杂役——董戈。因为董戈在拉胡琴的时候被大格格的副院长未婚夫听到,他觉得不错就推荐了来。命运的摆锤至此敲出沉重的声响,敲响了大格格宿命的倒计时。谁都说不清楚,一向目下无尘的大格格为什么会对谨慎卑微的董戈言听计从。
随着董戈对大格格的训练和鼓励,成就了她在义演舞台上的辉煌成功,到义演后大格格依然由董戈陪着操琴练曲,直到有关两人的风言风语传遍社会,宋家提出尽早完婚。大格格一天天尽是沉浸在和董戈二人的练唱当中,心无旁骛,风雨不改,完全不理身外事。“看得出他们彼此深深地依恋着对方,这种依恋诚挚而痴迷——谁是琴,谁是董戈?哪个是戏,哪个是大格格?分不出来了。他们已经没有了现实,艺术的唯美性在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深刻共识与和谐,实在是一种诗化了的感受,它让艺术家着迷的同时也蕴含着悲剧的到来。”他们的感情早就超越了男女爱悦之情。别人闹不明白,这俩人为什么能互相吸引。有人说是爱情,但大格格坚决否认,她认定她与董戈之间光明磊落;有人说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吸引,但为什么只吸引了大格格呢?还是金家的老七总结到:“什么也不为,就为了一个字:戏。”董戈和大格格其实都是受苦的人儿,别看大格格在现实中金尊玉贵,实际上命运不由她自己把握,她唯一能自由呼吸的时候,就是在戏里。贫穷的董戈就更是困苦无依,唯有胡琴是他生活的依托,与大格格的唱和就是他短暂的桃花源。这俩人唯有在戏里、在艺术里才能相依相偎,才能暂时忘却现实的悲苦。
直到大婚前的某一天,董戈没有上金家来操琴,之后也没有再来。董戈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消失了,金家人陪着大格格上门寻找,董戈消失得彻彻底底,之后几十年再也寻摸不着了。大格格仿若被抽去魂魄,她木木呆呆地完婚,木木呆呆地过日子。婚后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天天打扮好到护城河边独自练唱。她“坚信有一天董先生来了,她能以最佳状态迎接那渐臻至妙的胡琴,以精熟完美的唱腔面对她的琴师。”后来,丈夫出轨丢下她独自出国,公公婆婆在日本投降以后被当做汉奸处死,家产充公。大格格独自带着儿子生活在遗留下来的小屋里。她不愿搬回娘家住,也不向娘家开口要帮助,对儿子也是不管不顾,仍然持续每天去护城河练唱。再后来,儿子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夭亡了;大格格过不了几年也死了。
在大格格的故事结尾,叙述者“我”猜测,大格格在临终时应该是唱响了她在高光时刻的曲目:《锁麟囊》。
“一霎时把七情俱以味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
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
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叫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可怜我平地里遭此贫困,我的儿啊——
把麟儿误做了自己的宁馨。”
大姐金舜锦的故事完结了。
金家第二个反叛者——五哥金舜锫。他的故事不像大格格那样详尽,而是比较简短。作者采取分写的手法,在五哥的“本传”里只记述了他做过的荒唐事以及结局;而在五哥儿子金瑞的经历当中,适时插入和揣测五哥荒唐背后幽微曲折的心迹。
五哥和大格格为一母所生,同样爱唱戏。他的外貌在众子弟中最为清秀,小生唱得最好,曾拜名小生程继仙为师;小生之外,丑也唱得极好,“他的蹲步可以与专业水平比美,功夫不在当时名角之下。是真正下过苦工学戏的。不仅能唱戏,他还是金家众多子女中最活跃、最有才华的一个,聪明但浮躁,多情却不专;学不好好上却写得一手苍劲好字,书不好好读却说得一口流利外语;每天不是泡茶馆就是泡戏园子,跟一帮女艺人、女戏子打得火热”,活脱脱一个市井贾宝玉。这里正好可以用上曹雪芹给贾宝玉的判词之一: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五哥喜欢唱戏,想真正下海干专业,家里当然反对。票友玩玩可以,贵族家的子弟岂能真入梨园行。“不能去唱戏,就是街头的叫花子也比唱戏的有身份。”不能实现理想,五哥心里窝火,他赌气干些最荒唐的勾当。比如,“你不是说唱戏的下九流,叫花子有身份吗?我就给你当个叫花子,丢你们金家的脸!时不常的,老五就要披挂一番,破衣烂衫地走出家门,专门找前门、大栅栏这些热闹地方去讨要。”就是这样一个荒唐的公子哥儿,天分又恰恰是最高的,这更让父母痛心。他扮花子讨饭,被警察抓进收容所,家里不得不派人去把他领回来。父亲实在管教不了五哥,只好买了房子给他分家单过。没了父亲的管制,五哥更是无法无天,声色犬马,纸醉金迷,“或西装革履,满嘴洋话,以‘名士’面目出现在外交宴会上;或长衫尽碎,索饭哀号,以‘乞丐’嘴脸晃荡于街头;纳男宠,交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娶太太,又一个接一个地离婚”,花费巨资捣腾庭院住所,最糟糕的是染上了大烟瘾。总之,他把他想体验的都体验了一遍。不过,无论他再怎么折腾,他都紧守了父母给他的底线:没有做戏子。
当他从收容所被领回家,“脏烂不堪”地面对父亲的责备。他与父亲的对话,谁能说他没有过深沉的思考呢?
“父亲说:‘你总该干些什么才好,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你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呢?’”
老五“慢腾腾地说:‘生如寄,死如归,一蓑烟雨任平生。’”
“父亲说,‘凡做事,要多思量,无为亲者所痛。你的兄弟众多,哪个不能帮你,何苦到外头去讨要?’”
老五答道:“莫嫌憔悴无知己,别有烟霞似弟兄。”
到底老五为什么要这样作践自己,作践家庭呢?“为我们家老五的怪异举止,我曾经和一位研究社会学的专家讨论过,……专家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颓废。”戏痴的大格格和叫花子的五阿哥,其实都是颓废的。他们不事生产、不思进取,除了己身不思外物、不理外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困境,什么封建,但自由的灵魂会本能地感受到束缚。他们的叛逆不是与外界抗争,而是消耗自己,颓废就是他们的反抗。他们就这样由着性子把生命给他们的馈赠穷奢极侈地浪费掉。他们最后的结局都是横死,大格格在阴惨暗淡的小屋里油尽灯枯,五阿哥在隆冬夜晚倒毙在桥底下。
老五并不是一个没脑子的二世祖,身处动荡的时代交接点,风雨飘摇的大宅门,虽然父母尚在,兄弟众多,但他在胡闹的生活里早就看穿看透了。家庭是不稳固的,兄弟是不可靠的。事实上,在老五生前死后,金家的兄弟姐妹并不齐心,他们有自相残杀的(国民党的大哥间接导致共产党的三姐被处死),有见死不救的(文革中,三哥四哥导致二哥冤死),有凉薄决绝的(二姐私奔,后来的当家人三哥至死不与她见面),一家子兄弟姐妹在时代风云中七零八落。五哥的深心所想,要隔着悠长岁月,到了90年代,在他儿子金瑞的心里才起了回响。“这个贵族之家的败落,留给他的飘零子女们的真正遗产不是亲情,而是冷漠,这是金瑞到今天也不能理解、不能说清的一种情愫,也是他在京城随时感觉到孤立无助的茫然和清冷的原因。是的,在金家,他永远找不到‘世间最难得者亲兄弟’的认同,他永远是一个人,连他的梦境也是一个人踽踽独行。亲朋无一字,欲言无予和,这种发自骨子里的孤单是不是就是当年他父亲的感觉呢……”
老五的故事也结束了,金家很多子女的故事都结束了。从清初开始到康熙鼎盛再到清末飘摇,最后在新中国凋零,不仅是一户金家,还是其他八旗子弟家庭的缩影。叶广芩在小说后记里记述,之所以用采桑子及其词句作为小说名和章节名,“一方面是借其凄婉深沉的寓意,弥补本书之肤浅,一方面也有纪念先人的意思在其中。”因为这首《采桑子》的作者,正是叶广芩家史中的著名人物:纳兰性德。他的这首词曲曾被梁启超赞为“时代哀音”。
正如甄士隐解注《好了歌》,金家的历史也是《采桑子》的解注。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