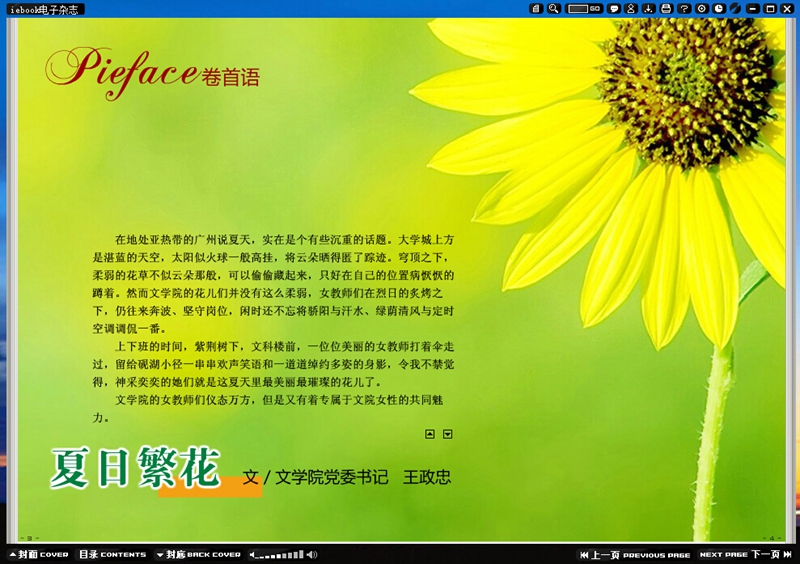西行地平线(上) / 海风






亚洲中心——乌鲁木齐
“以天山为书脊,新疆是一册打开的经典。南疆和北疆舒展辽阔的页码,混血的风景奇崛而起。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傍依两侧,两盆时间的黄沙,两页记忆的残简,沙漠无言的混沌映衬天山嘹亮的蓝。”
——沈苇《新疆词典》
“轰”地一声,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
背上硕大的背包,我快步走出喧嚣的机场大厅。
走出大厅的自动玻璃门,北京时间下午5点的热浪扑面而来。乌鲁木齐与北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因此,此时是阳光最猛烈的时候。
顺利坐上机场大巴,告诉司乘人员,我要到红山下车。红山位于乌鲁木齐市中心,我预订的麦田国际青年旅社就在红山附近。
我留意到,在地窝堡机场,深眼窝高鼻梁的维吾尔族的美女、帅哥开始出现,他们操着生硬的普通话与你交流,令人感觉异域风情明显增多。
我坐在窗边,不时向外张望。身穿民族服装的维族男女老少在街道两边随处可见,伊斯兰的建筑逐渐增多,这里是他们聚集的城市。我常常迷恋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置身在身穿不同服饰、操着别样的语言、高鼻梁深眼窝的少数民族聚集地,我充满了好奇心。
进入市区,路面的车辆开始增多,大巴的行驶速度也开始放慢。道路狭窄,人流量大,人车抢道,秩序混乱,加上路政施工,堵车是必然的。同其他城市一样,乌鲁木齐也同样面临着车辆增多,交通拥堵的城市发展困局。没有办法,城市配套设施、基础设施跟不上GDP的发展步伐,交通瓶颈的问题永远也无法解决。
途中见到乌鲁木齐的BRT,顿感亲切,其中一站是著名的“八楼”。歌手刀郎10年前的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提到“八楼”,红遍大江南北。“八楼”其实是乌鲁木齐市民对昆仑饭店的昵称,因为早期的乌市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8层楼高的昆仑饭店是当时的最高建筑,因此才被称作“八楼”。
一个多小时后,我来到红山。在青旅人员电话指引下找到了麦田。
我入住的是8人间,房间很大,两边各摆放两张上下床,还有很大的空间。不像内地的一些热点旅游城市的青旅,除了床之外几乎没有落脚的空间了。
放下行李,大致考察一下青旅内部环境,男男女女,金发碧眼老外还是蛮多的。除了卫生间不尽如人意之外,其他都应该无可挑剔。
走出青旅,抬头看看,离天黑还早,不如随处走走吧。
在一个十字路口,找了个汉族模样的男子上前询问大巴扎怎么坐车去。他上下看了我一眼,说道,傍晚最好不要去,要去明天白天可以去看看。我大吃一惊,莫非那里真有点恐怖的味道。我不甘心,过会儿再次上前找人询问,得到同样的建议,我只得放弃这个念头。临街的每家商店门口的玻璃上都贴着“开包检查”的字样,看着有点不敢进去。
附近就是红山公园,据说很值得一去,并且是免费开放。听说是免费的景点,我就会两眼放光。抓紧时间去,别等到了那里,却到下班关门的时间。
红山公园很容易找到。它是建在一处小山包上的公园,有亭台楼阁,登高可以观市景。红山是乌鲁木齐的标志和象征,它的驰名得益于山体呈赭红色的紫色砂砾岩,故得“红山”一名。这里还有一尊林则徐的雕像,纪念这位虎门禁烟、抗英有功,但却被贬发配到这里的民族英雄。
逛完红山,走回青旅。9点多的乌鲁木齐还是天光大亮,令我有点不习惯。来到新疆,一定要吃大盘鸡啊。想到大盘鸡,我开始猛咽口水。问过青旅的工作人员哪里有好吃的小饭馆之后,立刻直奔过去。
“老板,有没有小份的大盘鸡啊?”
“没有,只有中盘的大盘鸡。”维族小伙子用双手在身体前比划着中盘的大小。
我看看还是挺大,一个人吃有点浪费,何况价格还是蛮贵的。
“要不,来份椒麻鸡?!”,小伙子看我在犹豫,就说道。
“多少钱一份?”
“25块。”
“那就来一份。你们这儿能不能喝酒?”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因为伊斯兰教是禁酒的,我怕引起宗教冲突,就先问个清楚。
“可以喝酒。4块钱一瓶,乌鲁木齐啤酒。”
很快,酒、肉摆了上来。鸡肉酥麻可口,有点象广式盐水鸡的味道。就着鸡肉,我自斟自饮。在外旅游,我晚饭时一般会喝点啤酒,一来解暑,二来酒精可以麻痹一下大脑,便于睡眠,缓解疲劳。
坐BRT来到火车站,顺利地买到了第二天中午的车票。再去打听一下火车站附近的包裹寄存点的收费情况,我可不想第二天上午背着大包到大巴扎那里逛。
夜幕降临,华灯已上。来到乌鲁木齐,突然间,对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都市产生了一种抵触心理。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面无表情匆匆赶路的上班一族,高强度的生活节奏,步行商业街的空气里似乎也能嗅出铜臭的味道。
大门外的事情
我在2008年来过一次乌鲁木齐的大巴扎。巴扎,维吾尔语的意思是大门之外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商品交易集市。大巴扎里商品琳琅满目,光鲜照人的器皿、诱人的干果、美丽的维族姑娘一直在我脑海中浮现。当年正值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和同伴是沿古丝绸之路从兰州骑车到乌鲁木齐的。
早晨吃过早饭,退了房间,背着背包先来到火车站寄存背包,再坐车来到大巴扎。
可能我来的还太早,里面的商铺还没有开张。
二道桥如今已不仅是一座桥,而是一片街区——维吾尔族在乌鲁木齐最著名的聚集和商业区。外地来乌鲁木齐的游客慕名而来寻找的二道桥其实就是二道桥民族农贸市场,即二道桥“大巴扎”。
再次来到乌鲁木齐,二道桥依然是我愿意游逛的地方。那里极具民族特色的伊斯兰风格的圆顶建筑、来来往往高鼻梁深眼窝身穿民族服饰的维族同胞、熙熙攘攘的人流、琳琅满目的商品都可以让我一饱眼福。
现在的二道桥俨然成为乌鲁木齐这个城市的心脏。它的每一次跳动都可以激起城市血脉的高歌和喧闹。这里是古老与现实、世俗与神圣、商贸的喧嚣与宗教的肃穆完美的结合,是活生生的博物馆、舞台剧。
我走到大门处的墙边,找了个地方坐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
不远处停着一辆特警车辆,旁边站着一位全副武装,手持钢枪,头戴墨镜的防爆警察,他警惕地看着过往行人,以防不测。
看到此,我无语。都是东突分裂分子造成的紧张形势。我想,如果没有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背后支持,根本就不会有分裂祖国的恐怖势力生存的空间,西方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看看美丽的新疆,看看美丽的维族人民,各民族和睦相处有多好啊!
步入大巴扎,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令人垂涎欲滴的一排排的干果铺,一堆堆的葡萄干、巴达木、大枣、核桃、杏梅干被富有想象力的商家排列出美丽的图案。各种图案的毛毯、披肩挂满了店铺里的墙面,店家卖力地向过往的游客推销。
我慢悠悠地东张西望,宛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样,目不暇接。不自觉中我迈腿进入一个店铺,那里玻璃柜里摆满了来自印巴的工艺品,各式各样精雕细刻的化妆镜、手镯就足以让你挑选一两个时辰;还有那来自俄罗斯的精美器皿,银光闪烁,耀人双目。我融入在色彩斑斓言语杂多的人流中,每一样的商品源源不断地刺激着我的感官。
最后,虽然我空手而归,但这样的视觉冲击同样给我带来了精神上的享受与满足。
与城相恋,守望楼兰
鄯善,中国西部滨沙城市,楼兰人的第二故乡。长久以来,楼兰古国的消失,令世人惊叹。沙漠驼铃、古道孤烟的华美画卷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了。
中午坐上火车,来到鄯善县。
鄯善县是属于吐鲁番的一个县城。与沙漠为邻。这才是吸引我来这里的原因。
由此向东是令人生畏的漫无边际的沙漠,是死亡之地。由于时间短暂、经费有限、没有补给、支援跟不上、没有后勤保障,我也只能在沙漠边游荡一下。至于深入罗布泊、探寻古楼兰,那是考古学家、探险家的工作,与我相去甚远。当然,如有资助,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探访楼兰的征程。
鄯善县火车站离县城还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与人拼车来到县城,找了个家庭旅店住下,三人间,有空调,30元一个床位。来到这里,如果没有空调,嘿嘿,多半会变成干尸了。
放下行李,问过老板娘去沙漠公园怎么坐车。北京时间傍晚时分,正是爬沙的时候。
坐公共汽车来到沙漠公园,进门沿左侧小道前进,很快就看到起伏的沙漠了。
沙漠边缘的小沙丘上,一些老人小孩将腿或身子埋在沙子里,一边沙疗一边聊天。
古往今来,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吞噬了不计其数的城镇和生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文化宝库。这里是地球上唯一四大文明交融的地方。沙漠被称作“死亡之海”,斯文?赫定将塔克拉玛干翻译为“进得去出不来”,而维吾尔语的解释却是“古老的家园”。
塔克拉玛干处于新疆的“碗底”,但从精神海拔上去看,它恰恰占据了西域文明的一个灿烂顶峰。数百年来,无数个探险家、考古学家、盗墓者争先恐后地涌到这里,就是为了发现地下的文化宝藏。最后的结局却大相径庭,有人因此而成名、暴富,有人却命丧黄泉。
我来到起伏的沙漠,双脚踩在松软的沙子里,立刻感到了沙子的温暖。一位维族老妇人向我招招手,示意我坐下,像她们一样沙疗。我用手挖了个小坑,脱掉鞋袜,将双脚埋了进去。
哎呀,好烫,我差点喊了出来。脚底下磨破的水泡阵阵疼痛。
慢慢地,等双脚适应了沙子的温度后,我才仔细地观察这片银色沙漠。烈日偏西,但热度丝毫不减。炙热的阳光辐射和沙子的热度很快让我汗流浃背。而身边的维族老人们都在陶醉地享受着沙子的温度带来的体疗。
这是与戈壁相连的沙漠边缘,属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边缘的库木塔格沙漠。据说是距城最近的沙漠。
站在烈日下的荒漠中,我仿佛看到远处驼队在氤氲之中缓缓走来,聆听到了丝路驼铃的声音。
我想向沙漠腹地进发,就拔出双脚,穿上鞋子,两脚顿感轻松。其实,沙疗如同中药泡脚,能起到活血化瘀,消毒按摩的功效。我迈开双腿向远处高高的沙丘攀登。沙地上行走,异常地艰苦。由于脚下松软,脚踩下去后支撑点不稳,总是走一步退半步。
七月的新疆,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偏偏在这个酷暑时节来到吐鲁番的鄯善县,来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热度。无边无垠的沙丘,腾起逼人的热浪,汇合着强劲的热干风,直向我扑面而来,我的每一寸肌肤立刻感受到紫外线强烈的辐射。
我完全暴露在沙漠之中,顶着烈日,抬腿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向着沙漠深处迈进。我一边攀爬,一边心有余悸地想着路边“沙漠腹地,严禁进入”的警示牌。
或许听过太多的有关沙漠肆虐吞噬生命的可怕故事,每每想象这可怕的情景,都会让我毛骨悚然、心惊胆战。人们对沙漠的敬畏和恐惧,来源于沙漠巨大的破坏力。沙漠可以一夜之间扫荡数以万计的生命,是名副其实的流动的坟墓,是死亡之海。
我思量良久,还是决定在安全的范围内来一次谨慎的理性的沙漠探险。
来到陡峭的沙丘边,我喘了口气,背好相机,手脚并用地向上爬。前方有个瘦小的人影端坐在沙丘上,我迅速靠拢过去。长相很象欧罗巴人的维族小伙子示意我和他再向腹地深入。有当地同胞和我一同行走荒漠,我立刻底气十足。
起伏的黄沙在风的吹动下,呈现出波浪形状。再往深处,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流沙山丘,连绵浩瀚,一望无际。周遭景象像月球表面一样的死寂。
看着如此安详的沙漠,怎么也想象不出狂风大作、黄沙飞舞、遮天蔽日的场景。站在沙丘之上,可以看到远处葡萄沟的绿色点缀在沙漠与戈壁之间。
我站在沙丘之上不住地感慨,那些时断时续的绿洲连接起来的生命通道,又不得不与浩瀚的沙漠抢水。生命,在这里变得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仿佛整个生存的含义浓缩剩下的就只是朴素、顽强与乐观。
千百年来,鄯善绿洲与沙漠和谐相处,形成“绿不退,沙不进”的格局。当年古楼兰消亡后,一部分楼兰人穿越沙漠,来到鄯善定居。
时过境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流逝的不仅是时光,更是滚滚的沙尘。沙漠随风移动,河流也发生巨变。在昆仑山雪水汹涌的年代,河水流到沙漠腹地,绿洲扩展,草木昌盛,城郭繁荣。多年以后,各种原因造成河水稀少并且流程缩短,使得草木枯死,绿洲消失,城郭萧条,进而消亡。昔日的城垣村舍被遗弃在荒漠之中,古道也淹没在肆虐的流沙中。这就是楼兰古国的命运。
在沙漠中,每一处人居之地,都会有远处高山雪峰融化的雪水缓缓流淌而至。坚韧的白杨林在沿河的两岸整齐方正地把雪水包围起来,就好像他们把一片一片的由白杨和胡杨围栏起来的绿地安放在一望无际的黄沙之中一样,从高空鸟瞰,酷似棋盘上规则的网格。这就是“沙漠中的绿洲”,人们栖息休养之地。
即将进入的地域,正好可以提醒我们,对于自然,人类不能太过于狂妄,我们应该对自然心怀敬畏。人对自然的索取不能超过她的给予,不能超出自然的承载力,否则就会招致大自然的无情惩罚。
我们只需抹去故事里的神话色彩,就会发现,在这个半睡半醒的传说之梦中所蕴含的可拍的事实,以及人类破坏环境就必遭天谴的真谛。
夜幕慢慢降临,与维族小伙分手后,我开始往回走。很奇怪,随着光线的消退,本来烫脚的黄沙很快开始变凉。放眼望去,茫茫黄沙表面像有水气升腾一般,看上去湿气很重。我这才明白,当年三毛在写有关撒哈拉的故事时,提到深夜的撒哈拉沙漠冷的出奇,并非杜撰。
想着浩瀚的令人生畏的沙漠吞噬了多少的西域城郭,我也只能啧啧叹惋。
世外桃源——吐峪沟麻扎村
早晨起床后,老板娘过来问:“小伙子,昨天去沙漠公园没?今天可不能去啊。天气预报说今天45°。”
我立马窃喜,暗暗庆幸昨天已经去过。今天的打算是去吐鲁番或者去吐峪沟。
吐峪沟,我是在旅游书上看到的。一个在火焰山下的峡谷,是葡萄最早落户中国的地方。吐峪沟在维族语中是“走不通”的意思。麻扎村位于吐峪沟的入口,是中国伊斯兰教圣地,也是世界伊斯兰教七大圣地之一。传说穆罕默德的弟子易木乃哈等人最早来到中国传教,来到吐鲁番盆地,终于有一位当地的牧羊人成为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他去世后埋葬在吐峪沟的一个山洞里。因此,以后的每年前来朝拜的国内外穆斯林络绎不绝,号称“中国的麦加”。但由于交通不便,气候炎热,目前游客较少到达。
从鄯善没有直接到达吐峪沟的班车,除非包车过去。于是打消去吐峪沟的念头,准备坐班车直接到达吐鲁番。去吐鲁番除了想在周边游玩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4日要和燕大侠在吐鲁番会合。燕大侠本想暑假去云南游玩,结果被我“忽悠”来新疆,我怎么说也要迎接一下啊。
坐车来到吐鲁番已近中午,正在汽车站广场徘徊寻找落脚住宿的地方时,一位姑娘咋咋呼呼地过来问我要不要拼车游玩。她们三人,两女一男,刚到吐鲁番,晚上去库车的火车。因此,在吐鲁番也就只有半天的时间游玩。
好啊,如果四人拼车,交通费用是最划算的。今天不去游玩,明天我也要想办法找人拼车呢。想到这里,也就答应下来。
谈定价格,上车走人。游玩的地方是:吐峪沟、火焰山、交河故城、葡萄沟、坎儿井等著名景点。
“师傅,这火焰山能爬吗?”在开往吐峪沟的出租车上,我看着公路边不远的火焰山,好奇地问道。这大名鼎鼎的火焰山延绵百公里长,山体成褐色,山脊自下而上,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这里夏季温度常常超过45°以上,老版《西游记》的拍摄地选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谁爬这啊,这么热的天!”维族司机用新疆普通话回答我。
“哦,这山应该可以爬。”我自言自语。看着山的海拔并不高,应该能爬上去。
“亲,传说中的古铜色就是这么晒出来的。”我身边坐着的女汉子把手臂伸出窗外,故作夸张地说道。
盛夏的西域阳光干燥炽烈,我们坐在没有开空调的出租车上,开着车窗一路驰骋在广袤的戈壁滩上。此时,北京时间2:00时分,热风就像冲击波一样从窗外向我们袭来。
没错,我们坐着的出租车没有开空调。只因为在和司机谈价钱时,女汉子很天真地说,可以忍受不开空调。我真怀疑她不是被驴踢了就是热糊涂了。
“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热呢?!”女汉子继续咋咋呼呼地说着,然后补充道“我是不是有点变态。”
“你好像已经热糊涂了,有点像在说胡话。”
车转过一个弯,路边开始绿树成荫,土黄色的泥巴墙砌成的房屋与背后的火焰山混为一体。残破的墙体、错落有致的村舍不就是我所中意的原生态嘛。
下车后才知道这就是我计划中的吐峪沟麻扎村。呵呵,有缘啊!
女汉子三人买票进麻扎村,我独自一人来到村口寻找住的地方。路边,车轱辘形状的大门吸引了我。走进院子,一排四面透风的顶棚下摆放着两张大大的床铺。几位维族妇女在吃饭聊天。
“请问,这里可以住宿吗?”
“你要过夜睡觉?”维族大嫂用生硬的普通话问我。
“是的,我一个人,多少钱?”
维族大嫂和家人用维语交谈了几句说:“二十块钱。”
我一听心中欢喜,指着床铺问道:“晚上就睡这里?!”
“是的,屋里太热,晚上睡不着。”
“那,能在这里吃饭吗?明天早上我就走了。”
“吃饭六十块。”
我按捺住心中的喜悦,答允下来。苍天有眼,让我回到了吐峪沟。
“怎么,你要在这住下?!”女汉子见我从出租车后备箱里拿行李,吃惊地问道。
“是啊,今晚我住这儿。”
“这里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洗脸用水壶,夜晚睡院中的村庄?!”
“是的。就是这里。”我斩钉截铁地说道。
吐峪沟,拥有两个圣地的圣地。
吐峪沟霍加木麻扎是世界伊斯兰教七大圣地之一,也是中国伊斯兰教最大的圣地,被誉为“东方麦加”。吐峪沟千佛洞是吐鲁番盆地规模最大、开凿最早的石窟群。在吐峪沟的山坡和崖壁上,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光芒交相辉映。
霍加木麻扎也叫艾斯哈布凯海夫麻扎,意思是“圣人居住的山洞”,也叫“七个圣人和一条狗的麻扎”。
相传7世纪初伊斯兰教初创时期,也门国的也木乃哈等六人带着穆罕默德的旨意前来东方传教。到达吐鲁番地区时,遭到当时的国王排斥和追杀。他们逃进火焰山中的吐峪沟,一位带着牧羊犬的牧羊人帮助他们躲进了山洞,这个当地人就成为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因此,这个山洞也就成为后来无数穆斯林朝拜的的圣地。
另外一个圣地就是吐峪沟的千佛洞。开凿于晋代的千佛洞大部分因天灾和人祸而塌毁。现存的洞窟不到一百个,我前去探访时,工人们正在维护施工中。
千佛洞位于火焰山峡谷的一角,两边山体色彩斑斓,呈现火焰状的一道道皱褶。山涧溪水顺着沟渠奔流而下,灌溉、养育了古老村庄。千佛洞在大峡谷的深处,需沿着河道向上游步行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