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辛亥革命纪念馆挑挑刺儿(文 / 杜新艳 文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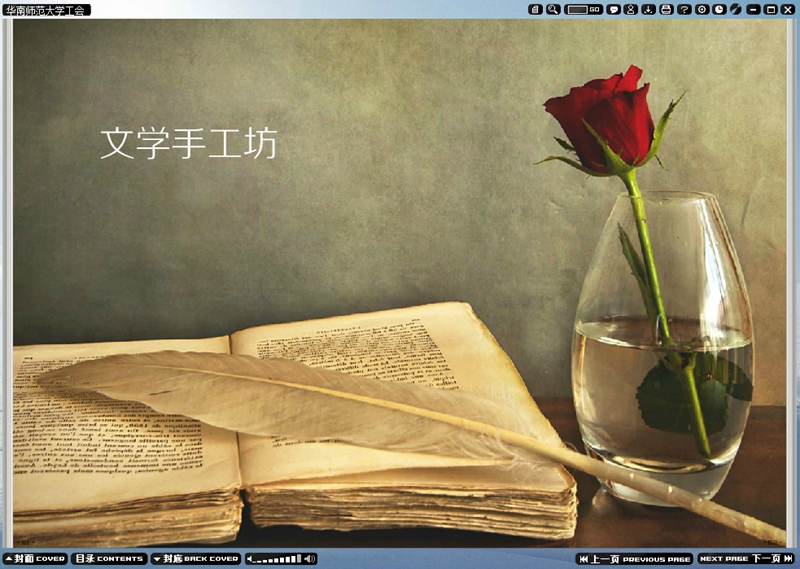

辛亥革命纪念馆自2011年10月开放,至今已有四年多了。从小谷围岛乘车到长洲岛,只是举手投足之劳,作为一名大学城人,我为我的迟到而抱憾。
从金洲大道看去,纪念馆平淡无奇。方方正正的建筑有三层楼那么高,一度让人怀疑会否是什么厂房。走近了,仍未见任何纪念馆的标识,仅有一指示牌写着“参观请从正门走”,心想应该就是这里了。
独立于馆舍旁的石柱颇有点民族风格,花纹看起来像是麦穗。但这里毕竟不是在纪念农民起义,我不懂建筑,不晓得它是什么寓意。路旁的公园倒不失岭南的葱郁,洋溢着热情。长洲岛杨桃节旅游文化主题正热热闹闹地上演着,纪念馆显得有些门前冷落车马稀。
要进入展馆必须经过一条向上延展的坡路,即所谓的“共和之路”。路上穿插着一座座英雄雕像,似在缓缓而行,给人亲切感。路的尽头是孙中山先生的雕像,与行走在路上的英烈雕像相比,它显得非常威武,同时也非常孤独。
一踏入展馆,一幅巨大的屏幕吸引住了不少参观者,尤其是随行的小朋友。屏幕中运用多媒体技术,以动画的形式,借助近代漫画来再现晚清社会历史。第一展厅播放的是以谢缵泰的漫画《时局全图》为原型改编加工而成的动画。谢缵泰的《时局全图》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幅具有近代意义的漫画,常被选入中学历史教科书及相关文献中作为近代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最直观展现。而动画形式更将原来静止的画面生动丰富起来,原图中的熊、犬、蛙、鹰等野兽跳动不居,恣肆逞威,互相之间还争斗不休,有很强的形象性,也很有故事性。同时又用粤语画外音,沉痛地吟诵道:“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今宜醒,莫待土分裂似瓜。”这种形式一下子震撼了人心,再现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紧张形势。在近代岭南,革命派的漫画创作非常发达,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漫画报和漫画作家。如香港郑贯公主持的《世界公益报》,特别是潘达微主持的《时事画报》,一纸风靡,于是又有《时谐画报》《滑稽魂》等漫画报的兴起。其中潘达微的漫画《龟仔抬美人》也被制作成动画在展厅里面播放。但相比而言,《龟仔抬美人》不如《时局全图》改编得生动,没有充分展开来演绎。
说起综合运用各种媒体技术以及艺术表现手法,的确可算是辛亥革命纪念馆中颇具创新意识的一个表现,这种形象手法很值得发扬。不少经典的历史场景,通过电影、动画、油画、高分子硅胶人像以及场景立体还原手法,相当鲜活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但形象的表现方法需要较高的艺术创造性思维来支持,否则只能流于形式,而不能取得真正感人的艺术效果。同时艺术的形象思维又要符合历史现实,否则会贻误后人,歪曲真相。比如说在展示辛亥广州起义的时候,出现了喻培伦掷炸弹这个典型形象的雕塑。其设计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喻培伦身体后倾,表现出一种夸张的力量,而他的身上用线穿满了圆溜溜的手榴弹,洋溢着革命的激情。但1911年喻培伦自制的炸弹能否如此精致,很可怀疑。据目前的记载来看,辛亥革命成功之前的炸弹,大多是购买炸药后,由懂技术的人员手工制作的。喻培伦就以擅长炸弹制作技术闻名。但无论他的技术如何高明,都达不到后知之明者想象的那种军工制成品的炸弹精良。另外,有文献曾指出,当时喻培伦在战斗中,身前挂着一个装有炸弹的小竹筐冲锋作战,炸弹用完了才被捕的。辛亥广州起义仓促起事,恐怕喻培伦等真的没时间将自制炸弹精美包装,并穿成炸弹珠来搞行为艺术。艺术再现这段历史的时候,该如何把握分寸,艺术家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必须注意。在这个历史纪念展览馆中,我认为应以还原历史真相为上策。
其实,辛亥革命纪念馆在强调历史真相方面非常讲究,这令我很感动。在纪念馆内陈列着许多极为宝贵的文物真迹,据说有六七千件。看过许多纪念馆,像辛亥革命纪念馆这样用真迹说话的并不多。其中,包括孙中山随身携带的密电译码本、湖广铁路债券、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等流传海外多年的珍贵历史文物,还有更多鲜活的日常用品、衣物、枪械、旗帜、纪念章……。还有不少报刊书籍等文献资料,也都尽量取原刊实物而不以复制本代替,其中有些并不常见。这令一个曾翻阅过不少清末民初报刊的人置身其中,也常有如获至宝之感。尽管隔着玻璃橱窗,但只那一眼,对于渴慕了解近代、想要努力还原历史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慰藉。因为这些文物非常宝贵,所以橱窗都有恒温保护。此外,上下台阶处设有方便轮椅行走的专业轨道,这些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也是馆内值得肯定的措施。这一切都可以看得出纪念馆的确是精心营建而成的。相比而言,我前面有些想法显得吹毛求疵了。
但辛亥革命纪念馆的展示部分的确有些硬伤,错到了让我难以置信的地步。展览馆的基本内容,多是通过文字和图片展现主题。辛亥革命纪念馆在讲到近代的文学家们通过自己的一枝笔来揭露晚清社会的黑暗腐败,呼唤社会改良、民主革命时,张贴在展墙上的大图和所配的文字介绍之间大多是不对应的。比如关于小说家李伯元的文字,配图却是小说家刘鹗的头像;说明刘鹗的部分,对应的头像却是革命派作家金天翮;解说小说家曾朴的时候,展示的却是岭南诗人黄节的照片;介绍翻译家林纾时,却又配上了李伯元的图像。此外,岭南著名小说家黄小配的图片也有问题,目前我了解的黄小配形像是戴眼镜、西装革履,而展馆所配形象令我非常陌生。为此我专门请教了近代人文领域的一些专家。夏师晓虹指出是林纾的一张旧照,但因角度问题,与他平时的形象有点出入。左图右史、上图下说,在插图和文字之间,出现如此大的差错,在我是闻所未闻。我想,大约是制作过程中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才会有这样离谱的张冠李戴。但事后竟然没有专业人士审查核对,这倒有些奇怪。其实只要稍动动手,简单上网搜索一下即可。可是,从开馆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差错竟然还摆在那里,我不得不替各位地下的前贤担忧了。变得高度紧张的我,也开始担心辛亥革命纪念馆的其它展示部分也有类似错误,所以展览看得不那么顺畅了。但其他方面非我专业所长,即便有错,我也不容易察觉,且时间有限,只好放松警惕,匆匆走完了各展厅。
由于去得仓促,还有近代广东名人展和孙中山之女孙婉的一生等展览没来得及看。乘直梯下楼后,发现无路可走,只好又爬上去返回原地,重走了一回“共和之路”。又多看了一眼章太炎先生的雕像,实在觉得不像。有了场内错位的经验,这次我倒宁愿艺术家也是对错了号才雕刻得不像太炎先生,因为不愿相信艺术家的感觉会那么失真。太炎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是英气逼人的,但“共和之路”上的雕像却让人觉得弱不禁风,脸形过于瘦削,气质过于孱弱,神情过于颓丧。
走出正门,回望整个辛亥革命纪念馆,这才发现,它的外形竟然如一块石头,朴实无华。只是这块石头太过人工化了,被切割得方方正正,如同建筑用料,它缺少山间之石的自然灵动,也没有观赏石的丰姿雅韵。
辛亥革命纪念馆的定位是要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内容丰富、感召力强的顶级大型革命历史专题纪念博物馆。我觉得就目前而言,恐怕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其原因值得有关部门去思考和关注。但最起码,常识性的错误应该尽快更正。


